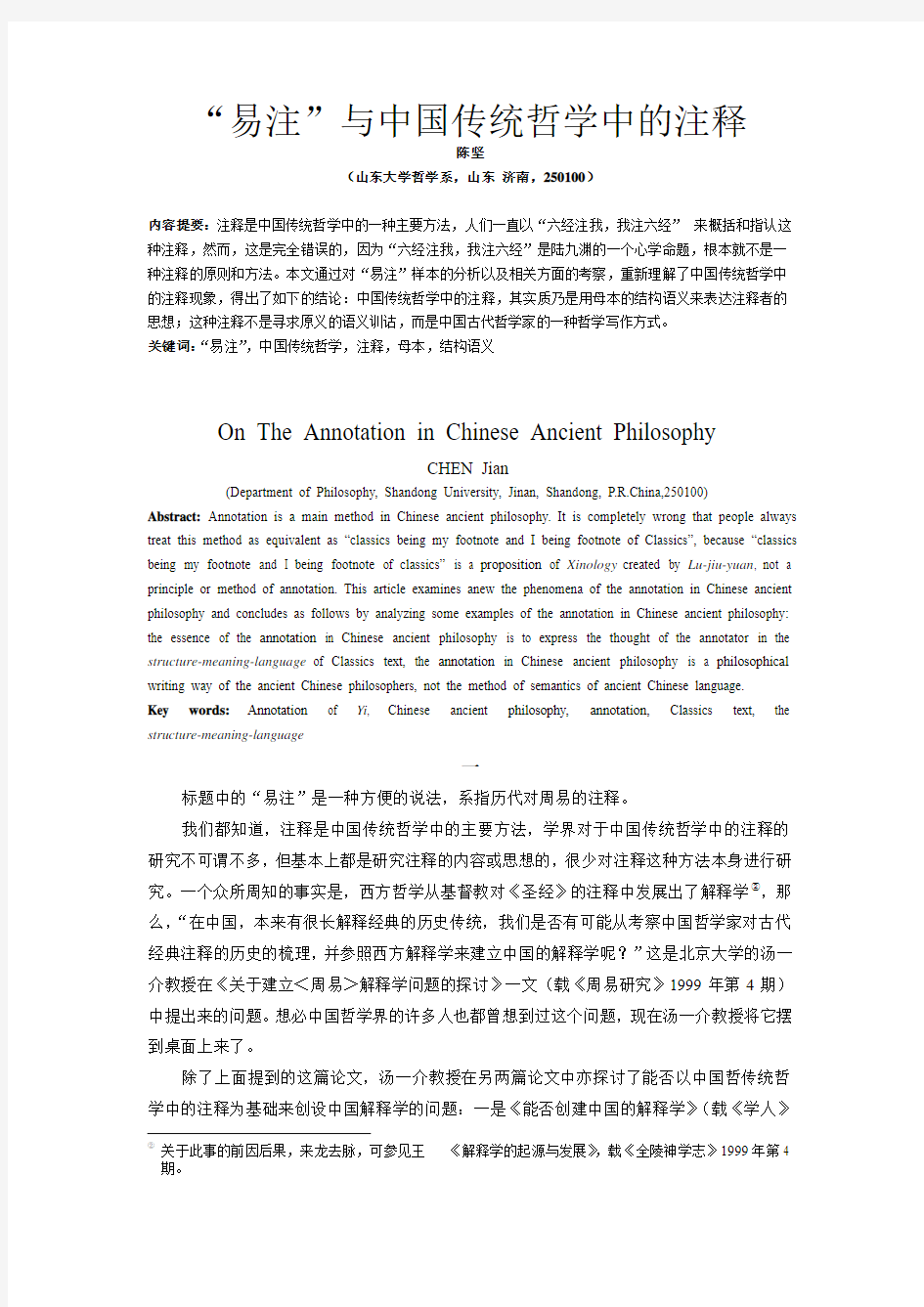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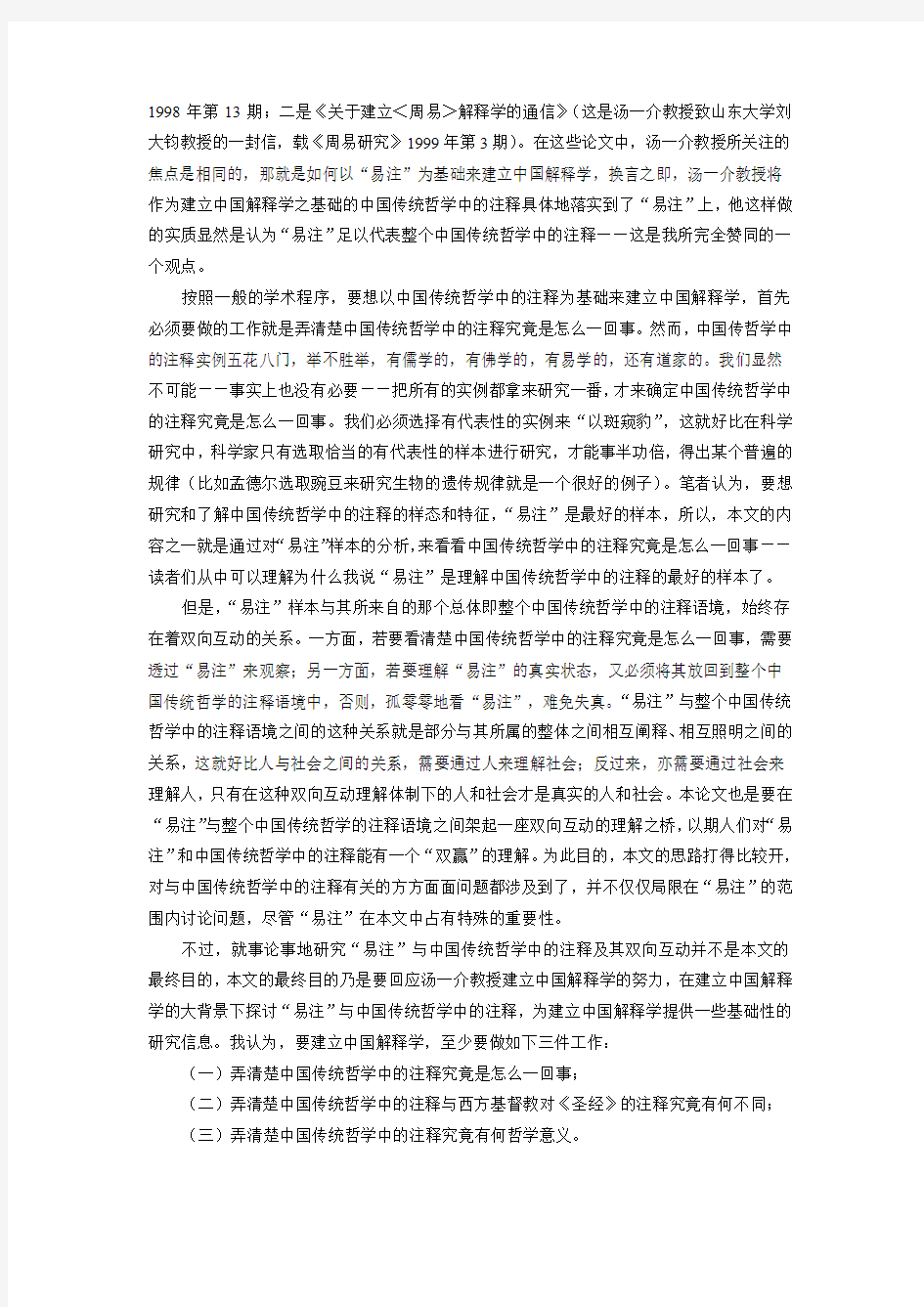
“易注”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
陈坚
(山东大学哲学系,山东济南,250100)
内容提要:注释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种主要方法,人们一直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来概括和指认这种注释,然而,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陆九渊的一个心学命题,根本就不是一种注释的原则和方法。本文通过对“易注”样本的分析以及相关方面的考察,重新理解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现象,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其实质乃是用母本的结构语义来表达注释者的思想;这种注释不是寻求原义的语义训诂,而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一种哲学写作方式。
关键词:“易注”,中国传统哲学,注释,母本,结构语义
On The Annotation in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y
CHEN Ji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P.R.China,250100)
Abstract: Annotation is a main method in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y. It is completely wrong that people always treat this method as equivalent as “classics being my footnote and I being footnote of Classics”, because “classics being my footnote and I being footnote of classics” is a proposition of Xinology created by Lu-jiu-yuan, not a principle or method of annot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anew the phenomena of the annotation in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y and concludes as follows by analyzing some examples of the annotation in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y: the essence of the annotation in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y is to express the thought of the annotator in the structure-meaning-language of Classics text, the annotation in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y is a philosophical writing wa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s, not the method of semantics of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Annotation of Yi,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y, annotation, Classics text, the structure-meaning-language
一
标题中的“易注”是一种方便的说法,系指历代对周易的注释。
我们都知道,注释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主要方法,学界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基本上都是研究注释的内容或思想的,很少对注释这种方法本身进行研究。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西方哲学从基督教对《圣经》的注释中发展出了解释学②,那么,“在中国,本来有很长解释经典的历史传统,我们是否有可能从考察中国哲学家对古代经典注释的历史的梳理,并参照西方解释学来建立中国的解释学呢?”这是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教授在《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问题的探讨》一文(载《周易研究》1999年第4期)中提出来的问题。想必中国哲学界的许多人也都曾想到过这个问题,现在汤一介教授将它摆到桌面上来了。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篇论文,汤一介教授在另两篇论文中亦探讨了能否以中国哲传统哲学中的注释为基础来创设中国解释学的问题:一是《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载《学人》
②关于此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可参见王《解释学的起源与发展》,载《全陵神学志》1999年第4 期。
1998年第13期;二是《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的通信》(这是汤一介教授致山东大学刘大钧教授的一封信,载《周易研究》1999年第3期)。在这些论文中,汤一介教授所关注的焦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如何以“易注”为基础来建立中国解释学,换言之即,汤一介教授将作为建立中国解释学之基础的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具体地落实到了“易注”上,他这样做的实质显然是认为“易注”足以代表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这是我所完全赞同的一个观点。
按照一般的学术程序,要想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为基础来建立中国解释学,首先必须要做的工作就是弄清楚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然而,中国传哲学中的注释实例五花八门,举不胜举,有儒学的,有佛学的,有易学的,还有道家的。我们显然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实例都拿来研究一番,才来确定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必须选择有代表性的实例来“以斑窥豹”,这就好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只有选取恰当的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研究,才能事半功倍,得出某个普遍的规律(比如孟德尔选取豌豆来研究生物的遗传规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笔者认为,要想研究和了解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的样态和特征,“易注”是最好的样本,所以,本文的内容之一就是通过对“易注”样本的分析,来看看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读者们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说“易注”是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的最好的样本了。
但是,“易注”样本与其所来自的那个总体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语境,始终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若要看清楚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需要透过“易注”来观察;另一方面,若要理解“易注”的真实状态,又必须将其放回到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注释语境中,否则,孤零零地看“易注”,难免失真。“易注”与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语境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部分与其所属的整体之间相互阐释、相互照明之间的关系,这就好比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人来理解社会;反过来,亦需要通过社会来理解人,只有在这种双向互动理解体制下的人和社会才是真实的人和社会。本论文也是要在“易注”与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注释语境之间架起一座双向互动的理解之桥,以期人们对“易注”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能有一个“双赢”的理解。为此目的,本文的思路打得比较开,对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有关的方方面面问题都涉及到了,并不仅仅局限在“易注”的范围内讨论问题,尽管“易注”在本文中占有特殊的重要性。
不过,就事论事地研究“易注”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及其双向互动并不是本文的最终目的,本文的最终目的乃是要回应汤一介教授建立中国解释学的努力,在建立中国解释学的大背景下探讨“易注”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为建立中国解释学提供一些基础性的研究信息。我认为,要建立中国解释学,至少要做如下三件工作:
(一)弄清楚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二)弄清楚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与西方基督教对《圣经》的注释究竟有何不同;
(三)弄清楚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究竟有何哲学意义。
其中第一件工作是建立中国解释学的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本文所着力要做的工作,尽管
我不一定能把它做得很完美,甚至也有可能完全做错,但这是我热切的心意。
二
注释虽不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唯一的方法,但却毫无疑问应是占第一位的方法。注释在建构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由于注释的方法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被如此广泛地使用,以致于人们见怪不怪,对它缺少深入细致的考察,往往认为这种方法无非就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然而,笔者认为,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来概括和指认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是不妥的。
考诸来源,“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乃是陆九渊提出来的。《陆九渊集·语录上》载曰: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韩退之是倒做,盖欲因学文而学道。[1](P399
同书的另一个地方又载曰:
《论语》中多有无头柄的说话,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类,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学而时可之”,不知时习者何事。非学有本领,未易读也。苟学有本领,则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时习之,习此也。说者说此,乐者乐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1](P395)另,《宋史·陆九渊传》载曰:
(陆九渊)尝谓学者曰:“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缺,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与溺于利欲之人言犹易,与溺于意见之人言却难。”或劝九渊著书,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曰:“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2](P12881)
综合上述这三段引文,我们分明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一)“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并不是一种注释行为,因为注释是古代著书立说的一种主要写作方式(如朱熹著《四书集注》),如果“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一种注释行为,那么陆九渊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为自己的不著书辩解就是自相矛盾。(二)“学苟知道(或学苟知本,或学有本领①),六经皆我注脚”乃是对“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进一步解释,因此,理解“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关键就是要理解“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这句话。“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的含义可作如是分析:“六经”中所说的都是带普遍性的话,没有具有所指(“无头柄的说话”),比如《论语》中所说的“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和“学而时习之”都没有具体指明究竟知之所及者何事,仁之所守者何事以及时习之者何事,但是一个人如果真正地领悟到了“不必它求”、“我”自固有之“道”–––––当然是指“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的儒家伦常之道①,那他就会明白“六经”中所说的就是“此道”,“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时习之,习此也。”这就是说,“六经”中所说的,其实都是“我”自固有之“道”,而不是说了别的什么;反过来,“我”自固有之“道”也都体现在“六经”的文字之中,而不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与“六经”之间具有同一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陆九渊才说“六经
①这里的“本领”,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本事”、“能耐”或“能力”之义,而是“本”和“领”的合称,是“根本”的意思,其中的“领”是“要领”、“提纲挈领”之“领”,也是“本”的意思。
①明代王应麟在《国学纪闻·经说》中将陆九渊“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诗化为“日用是根株,文学是注脚”,其中的“日用”两字即是儒家的伦常之道。
注我,我注六经”,“六经”与“我”互为“注脚”②。既然“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六经”中都已表达和体现了“我”自固有之道,那“我”陆九渊还有什么著书之必要呢?但是陆九渊认为,从根本上来说,“道”在“我”中,“六经”充其量也只是“道”的记载而已,所以学道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而不能求之于“六经”之文–––––这实际上就是陆九渊“内求诸已”的心学理路。韩愈的“文以载道”思想与陆九渊的这一心学理路相反,认为“文”中(既然)有“道”,就应从“文”中学“道”,“因学文而学道”,故陆九渊斥之为“倒做”。
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所谓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根本就不是什么注释的方法,而是陆九渊根据自己个人的哲学实践而得出的一个哲学命题,用来表示“我”–––––一个儒家伦常实践者––––与“六经”之间所具有的同一关系③,这种同一关系其实就是陆九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学思想的一个具体表现(“六经”是圣人之心之理,“我”与“六经”的同一就是“我”与“圣人”同心同理)。当陆九渊用“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来表示“我”与“六经”之间所具有的这种同一关系时,他实际上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然而,人们不究其实,望文生义,以为其中有一个“注”字,就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当作一种注释的行为或方法来看待④,并用它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现象,这就离题万里了。
三
既然“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连注释的方法都不是,那我们显然就不能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方法归结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那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表面上看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方法无非就是古汉语语言学中的训诂方法而已,正因如此,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所有注释作品都成了训诂学家们理想的研究材料。我们都知道,古汉语语言学–––––即传统上所谓的“小学”––––––有三个分支,一是文字学,研究字形;一是音韵学,研究语音;一是训诂学,研究语义。训诂的方法也就是探索并确定母本(指被训诂的古汉语文本)语义的方法,当这种方法被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用来注释经典––––––这也是一种哲学写作方式––––––时,https://www.doczj.com/doc/8213017522.html,an说,“中国哲学就是语义学”(Chinese philosophy is philology)[3](P34)
然而,当我们说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就是语义训诂时,一个问题马上就出现了:因为
②考诸文献,“注脚”一词源自于禅宗的一则名叫“洗脚”的“公案”,该“公案”是这样的:赵州游方到院,在后架洗脚次,师便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赵州云:“会即便会,啖啄作甚么?”师便归方丈。赵州云:“三十年行脚,今日错为人下注脚。”(《佛光大藏经·语录部·五家语录》第41-42页)。这则“公案”中的三个主题词分别是“洗脚”、“行脚”和“注脚”,参这则“公案”就是参这三者的关系。
③对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赵林先生还有一个更为离谱的误解,他认为“西方学者做学问常给人以大气磅礴之感,多采取宏观立论、六经注我的方法”;而中国学者做学问则“过于注重训诂考据、旁征博引”,多采取“我注六经”的方法。最后,他说,中西学术之差别“或许就是‘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差别。”参见赵林《“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中西治学方法论的差异》,载《开放时代》1997年3、4月号,第18-21页。另外,美国汉学家Gianni Criveller (汉名柯毅霖)于1999年12月3日在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个讲座––––笔者曾亲聆此讲座––––中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翻译成favorable interpretation (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这显然也是不对的。
④因为人们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当作一种注释的行为,所以往往将其倒说成“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这显然是不对的–––––以突出“我注”的动作性。实际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中的“注”并不表现为一种动作,而是表现为一种状态。
语义训诂的目的只是要尽可能忠实地解释母本的语义,所以它经常象其他两门“小学”一样,被称为是“无思想的学问”或“不需要思想创新的学问”;而作为一种哲学方法,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显然要表现出思想性或思想的创新性,若非如此,它就不能算是“哲学的”,既是“哲学的”,就要有思想,就要有思想之创新。纵观中国传统哲学史,从先秦到明清,从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哲学思想的发展和创新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发展和创新,注释在其中起到了主要的和根本的作用。这个哲学史事实说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虽然从形式上讲是一种语义训诂,但又不是用语义训诂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
我们不妨以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具体的注释实例来印证上述观点。比如智旭在《中庸直指》中对《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作了如下的注释:不生不灭之理,名之为“天”;虚妄生灭之原,名之为“命”。生灭与不生灭和合,而成阿赖耶识,遂为万法之本,故谓之“性”。盖天是性体,命是功能。功能与体,不一不异,犹波与水也。……此节且辨性修,下文方详示因果差别耳。夫“天命之谓性”,真妄混而难明;“率性之谓道”,善恶纷而杂出。研真穷妄,断染育善,要紧只在“教”之一字。全部《中庸》,皆“修道”之“教”也,故曰“自明诚谓之教”[4](P465)这显然是在用佛学思想来解释《中庸》首句,至于整部《中庸》,智旭则认为,是在谈佛教的“不二心源”[4](P315)①。谁都知道,《中庸》是地地道道的儒家经典,里面是不可能含有佛学思想的,这一点其实智旭在写作《中庸直指》时也是清楚的,他在《四书禅解·自序》中说:“今夏……偶以余力,重阅旧稿,改窜其未妥,增补其未备,首论《论语》,次《中庸》,次《大学》,后《孟子》。《论语》为孔氏书,故居首。《中庸》、《大学》,皆子思所作,故居次。子思先作《中庸》,《戴礼》列为第三十一,后作《大学》,《戴礼》列为第四十二,所以章首‘在明明德’,承前章末‘子怀明德’而言,本非一经十传,旧本亦无错简,王阳明居士已辨之矣。孟子学于子思,故居后。”[4](P315)智旭清楚地知道,《中庸》是儒家传承中的著作,但是他却“明知故犯”,居然还用佛教的知识和道理来注释《中庸》,这种以佛释儒的现象难道可以用训诂一言以蔽之吗?
四
既然从训诂角度我们已无法圆满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现象,那么一种新的解释就成为必须。我现在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中注释现象的假说,以求教于方家。
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就注释者的动机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之为“寻求原意”的注释,另一类可称之为“寻求表达”的注释。所谓“寻求原意”的注释,是指注释者努力探明母本(指被注释的经典)的原意究竟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哲学家大都有一种强烈的“道统传承心态”(亦称“韩愈心态”),这在儒道佛易四家都是如此。在这种心态下,哲学家们都以正统自居,都认为只有自己才真正懂得祖上经典的含义,别人都理解错了,因此都要对这些经典重新加以注释,发掘出其中的“原意”,以恢复道统,比如王弼注《老子》,黄蘖禅师注《金刚经》,朱熹注《四书》,不一而足(至于这些注释最终是否
①所谓“不二心源”,无差别曰“不二”;心为万法的根源曰“心源”。“不二心源”即一切诸法无差别,皆是心之所生。
真的就达到了“原意”,且放在后文去说)。
所谓“寻求表达”的注释,则是象智旭那样,虽然知道《中庸》母本的原意是儒学的思想,但却偏偏还要用佛学的思想来注释《中庸》母本,他这样做的实质,乃是想借《中庸》母本来表达佛学思想①。在他的另一部著名的注释作品《周易禅解》中,智旭更是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寻求表达”的注释动机。比如,对于《比卦》“六二”爻辞“比之自内,贞吉”,智旭如是注释:
柔顺中正之臣,上应阳刚中正之君,中心“比之”,故“贞”而“吉”也。
佛法释者:欲天有福,亦复有慧,但须内修深定,又通教界内巧度,与圆教全事即理相同,但须以内通外。[4](P463)
这个注释分两段,第一段解释“六二”爻辞的原意,第二段以佛学思想来注释该爻辞(整部《周易禅解》都是这种两段法的注释)②。智旭明明知道“六二”爻辞的原意不是佛学思想,但却还要用佛学思想来注释它,其用心十分明显,那就是要借“六二”辞来表达佛学思想。
除了《中庸直指》和《周易禅解》,智旭的另三部著作《论语点晴》、《大学直指》和《孟子择乳》(已亡佚)以及憨山德清的《大乘起信论直解》、康有为的《论语注》、杨仁山的“发隐系列作品”③等也都是典型的“寻求表达”注释作品。不过,“寻求表达”的注释现象,最突出的还是存在于对《周易》的注释即“易注”中。从“易注”的第一部作品《易传》起,中国古代哲学家就不断地用儒学、道学、佛学思想来注释《周易》,同时还有从哲学以外的角度来注释《周易》的。《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一》曾对中国两千余年来的“易注”作了如下的总结: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易者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清代的杭辛斋甚至还从法律的角度来注释《周易》,认为“贲卦”、“丰卦”和“噬嗑卦”简直就是西方式的“司法独立之明证”[5](P144-115)。今天,更是出现了所谓的“科学易”,人们从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中医学、信息科学、宇宙学、管理学等现代科学角度来注释《周易》。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些五花八门的注释表明了《周易》中原本就包含着
这么多的取之不尽的知识、思想和学科内容①。冯友兰先生曾对“易注”中的这种独特现象作过解释,他认为《周易》本身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事物,它只是一些公式,这些公式犹如“空套子”,任何事物都可以套进去,是谓“神无方而易无体”[6](P7);而一般的人则普遍认为,
①智旭生活在晚明禅宗没落的时代,为了挽救禅宗,重整佛门,智旭毕生致力于融通儒佛的工作,希望借儒学来显扬佛学,而他作这项工作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借儒学母本来表达佛学思想。
②所以,在《周易禅解·自序》中,智旭写道:“或问曰:子所解者是“易”耶?余应之曰:然。复有视而问曰:子所解者非“易”耶?余应之曰:然。又有视而问曰:子所解者非“易”耶?余亦应之曰:然。更有视而问曰:子所解者非易非非易耶?余亦应之曰:然。参见[4](P1)。
③包括《论语发隐》、《孟子发隐》、《道德经发隐》、《冲虚经发隐》和《南华经发隐》等五部以佛学思想解
释儒道经典的作品。
①比如汉代的“卦气说”,以二十四节气来注解《周易》,然而,谁都看得出来,《周易》中何曾有二十四节气?
对《周易》的这种注释无非是将其他的知识、思想和学科内容比附或附会到《周易》上②。
我不同意冯友兰先生的见解,因为凡是公式都是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限定的,一个公式不可能象“空套子”一样可以套在任何事物上,而且《周易》本身也不是不涉及任何具体事物,不是象冯先生所说的是“易无体”,比如《周易》的卦辞和爻辞就十分具体,它们都是有具体所指的。至于一般人所谓的“比附或附会”,我也不能赞成,因为如果说用各种知识、思想和学科内容来注释《周易》就是在把各种知识、思想和学科内容比附或附会到《周易》上,那各种知识、思想和学科内容之间也应该可以互相比附或附会,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易注”的实质乃是在用《周易》母本表达各种知识、思想和学科内容,这就是《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谓的“援易以为说”。在“援易以为说”的注释中,《周易》母本其实担当着语言的角色,这种语言可称之为“语义语言”(semantic language)。因为《周易》本身的卦辞、爻辞或卦画、爻画都是有自己的语义的③,人们在注释《周易》的过程中,将这些语义语言化,并用这些语义来表达各种知识、思想和学科内容,这就是所谓的“寻求表达”的注释。
我们上文说到,就注释者的动机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可分为“寻求原意”的注释和“寻求表达”的注释两种,但即使是那些“寻求原意”的注释,注释者一旦进入具体的注释操作,“寻求原意”的注释随即也就变成了“寻求表达”的注释,注释者此时已很少去注意和发掘母本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实际上,有的母本,就象陆九渊在评论《论语》时所说的,都是些“无头柄的说话”,其原意是根本无法考查出来的),而纯粹是借母本的语义来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比如,自古以来,对《论语》的注释不计其数,不同的注释者都从中注出了不同的内容,并都声称自己所注的是《论语》的原意,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论语》的原意肯定只有一个,不会有那么多的“原意”。从理论上来说,在那么多的《论语》注释中,充其量也只能有一个注释是符合原意的(也有可能一个注释也不符合原意),其他的注释都是在“暗渡陈仓”,借《论语》母本的语义来表达注释者本人的思想,即这些注释都是“寻求表达”的注释。人们以前通常将这种注释现象称为“六经注我”,然而我们在前文已阐明,“六经注我”并不是一种注释的原则和方法,所以用“六经注我”来指认那些“寻求表达”的注释是错误的。
五
实际上,语义语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将语义语言化,用语义来表达思想的例子在我们日常的语言使用中是非常普遍的,比如在“我们公司今年创利100万,明年决心更上一层楼,创利150万”这句话中,“更上一层楼”就是用语义语言来表达的典型例子。人们一般的看
②比如刘立夫在谈到以古代数学注释《周易》时说:“《周易》与数学的关系,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后人在注解《周易》的过程中将古代的数学成就附会到《周易》上的一个结果。我们很难断定,《周易》本身就有这些数学理论。”参见刘立夫《周易与科学:一个容易神化的议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0年第10期第4页。
③在《周易》中,爻画、卦画也象爻辞、卦辞一样是“易语”,有着自己特定的语义,如“–––”是阳,“――”是阴,“≡”是“天”、“父”、“健”、“马”、“首”、“西北”、“秋冬间”的意思等等,参见陈凤高《周易白话精解》,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8页。
法是,“更上一层楼”是比喻,这是不错的,我并不否定从语法修辞上来说“更上一层楼”在这句话中是一个比喻,我所说的用来表达的“更上一层楼”的语义就是一个比喻语义,而不是字面语义或别的什么语义。我这里要说的是,这句话的作者并不是用“更上一层楼”这五个字来表达(这叫用符号语言来表达),而是用“更上一层楼”的比喻语义来表达。这个比喻语义,不但可以用在上面这句话中用来表达公司创利的情形,还可以用来表达其他种种情形,比如,“下学期,同学们应该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好的成绩”、“我们之间的关系日渐融洽,并且将会更上一层楼”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些句子中,“更上一层楼”的比喻语义已语言化了,具有了语言的功能,可以用来表达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认识,这就象“桌子”这个符号,可以用来表示各种各样的实在的桌子:三只脚的、四只脚的;圆的、四方的;木头的、塑料的……所以,在我们的语言表达中,可以用符号语言(symbolic language)来表达––––––即字面的(literal)表达,也可以用语义语言来表达[7](P64)。
在汉语中,语义语言是非常丰富的,一些古诗诗句(“更上一层楼”即是,另外如“道是无情却有情”)、歇后语(如“猪鼻子插葱–––––装象”)、格言(如“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俗语(如“说曹操曹操到”)和典故(如“三顾茅庐”)等都是语义语言的极好材料,只是其中的语义并不一定都是比喻语义罢了。关于这一点,恕不详细展开。我这里所要详细一说的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注释中,用来表达的母本语义主要是结构语义。所谓结构语义,指的是由语句的结构来决定的语义;而所谓语句的结构,指的是一个语句中的每一个部分,比如一个字、一个词或一个词组的意义都是相互联系的,当我们确定其中一个部分的意义时,其他部分都会为保持语句意义的完整性而随之产生相应的意义,也就是说,语句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意义同时也都隐含并指示着其他部分的意义。各部分的意义是“互在”的。比如在“衣服破了”这句话中,“衣服”可以指西装,也可以指衬衫;可以指大人的衣服,也可以指小孩的衣服;而且广义而言,这“衣服”还可以指裤子或裙子,而当“衣服”指西装时,或指衬衫时,或指其他的服饰时,“破”的实际内涵或实际所指都是或都可以是随之不同或不尽相同的,有的“破”在领上,有的“破”在袖上,这就是说,这个句子结构中所包含的语义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无限的。假设有人来注释这个句子,他就可以凭需要用这个句子中的语义来表达各种相应的意思或指涉相应的情形,把它注释成放在衣厨里的衬衫被老鼠咬破了,或注释成小孩子的茄克衫被火苗烧了一个洞,等等。
虽然上面这个“衣服破了”的例子有点夸张,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就象上述注释“衣服破了”一样,是用母本的结构语义来表达的。母本语句结构中所蕴含着的多种多样的语义就象语言符号一样,可以用来表达各种各样相应的内容,这就是语义的语言化。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注例实例上来看一下用母本的结构语义所进行的表达。比如对于《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历史上的注释很多,智旭的注释已在前文具引,这里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人的注释。比如,朱喜对它的注释是: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
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8](P17)李光地对它的注释是:
“率性之谓道”,人多讲似孺子,怛恻生心意思。此乃仁之端,非“道”字本位。此句只平平说去,吾性中有仁,率之遂为父子之亲,吾性中有义,率之遂为君臣之义。大抵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在心则谓性,在事则谓道。[9](P111)
《中庸》首句的结构语义是由“天命”、“性”、“道”和“教”四者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这种关系在句子中比较明显清晰,故我特地选其作例子)。智旭、朱熹、李光地三人在注释中分别通过这种结构语义表达了各自不同的思想,这从具体的注释内容中可以一眼看出,不必多加解释。这里所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中庸》首句的结构语义。智旭抓住其中的“教”字(他说“要紧只在‘教’之一字”),以“教”为佛教,于是乎该句中其他部分遂为保持句子意思的完整而具备了佛教的含义;朱熹从理学“性即理”的思想出象,抓住一个“性”字,以“性”为理,于是乎该句中其他部分也为保持句子意思的完整而具备了理学的含义;而李光地则以“性”为人本有之仁义,顺此来确定该句的结构语义,并以这一语义来表达儒家的伦理思想。
既已弄清楚了中国传统学中的注释的实质是用母本的结构语义来表达注释者的思想,那么接下来的也是本文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哲学家不直接用符号语言来表达,而要如此麻烦–––––至少在外人看来是如此–––––间接地用语义语言来表达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追寻到古汉语本身。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直接用古汉语的符号语言进行表达的情形也是很多的,但是作这样表达的文本大都不是理论性极强的哲学文本,而是叙事性的历史、文学文本。中国古代的哲学文本一般都是注释体的,用母本语义来表达的,究其原因,正如T.W. Organ所说,作为一种象形的符号语言,古汉语并不适合于表达抽象的思想,并不适于进行理论性和系统性都极强的哲学论文的写作[3](P34)。为避免古汉语在哲学思想和写作上的这种局限性,中国古代哲学家们遂采取了注释体的写作方式,用母本的结构语义来进行哲学表达,而母本的结构语义,正如谢月玲所说,具有广阔的意义空间,可以用来作多元的哲学思考①。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家采用注释体来写作哲学论文,实在是扬长
①谢月玲是以《周易》和《论语》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的,她说:“卦象的说明文字虽较象本身落实,但可以看到的是仍以具体的事物作简易的叙述或概括,如上述之例及“潜龙勿用”、“飞龙在天”等语,因此在对文字的工具性掌握更为精确的后代,要对之作再诠释是有很大空间的。可以说《周易》一书具有朴素的原始性格,未经人文精确的分析割碎,近于自然,故保有多元思考的可能性(自然者,相对于人文,代表一种无限性)。次论《论语》。《论语》最不同于诸经的,在于其语录体的表达方式,而语录体较之成篇的文字论述较不严谨,思路结构松散,段与段之间无一定必然性关联,因此在环节的沟通自易产生见仁见智,即便独立一段对话来看,以其无前后文,没有特定背景,乃至范围限制,诠释上便较没有固定思路的束缚,此外语录体较一般学术论述在发展时间上早,又倾向平易的生活,作者非有意建构一理念,而只是如实的呈现个人及个人与他人环境的互动,看来零散却是最真实而完整、未经刻意切除、删选的材料。一言以蔽
避短的明智之举。当然,先秦时期的哲学写作方式并不是注释(《易传》除外),注释写作方式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不过,这也不违背古汉语不适于哲学论文写作的特性,因为先秦时期的哲学文本–––––它们都成了以后注释写作的母本–––––都是格言式的,而不是论文式的。
当然,中国古代哲学家之所以要用注释体进行哲学论文的写作,除了古汉语语言本身的限制外,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将母本“宗教经典化”,考虑思想传承(这一点前文已略有谈及),但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一旦进入了具体的注释操作,哲学家们便都使尽浑身解数,用母本的语义来表达了。
参考文献:
[1] 陆九渊. 陆九渊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3] T. W. Organ. Philosophy and The Self: East and West [M]. USA: Susquehan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4] 智旭. 周易·四书禅解[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96.
[5] 杭辛斋. 学易笔谈[M]. 天津: 天津古籍书店, 1988.
[6] 冯友兰. 代祝词[A]. 唐明邦. 周易纵横谈[C].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7] T. William R. De Jong. Did Hobbes Have A Semantic Theory of Truth?[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990. 1.
[8] 朱熹. 新刊四书五经·四书集注[M]. 北京: 中国书店, 1994.
[9] 李光地. 榕村语录·续榕村语录(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欢迎阅读本文档!
之,即《论语》与《周易》在这个基本质地上拥有相同的性格的,而这个性格使新的诠释有更宽广的可能性与自由度。”(参见谢月玲《对“经学玄学化”一词与其现象背后意义之重审》,载台湾《人文学报》民国86年第3期,第7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