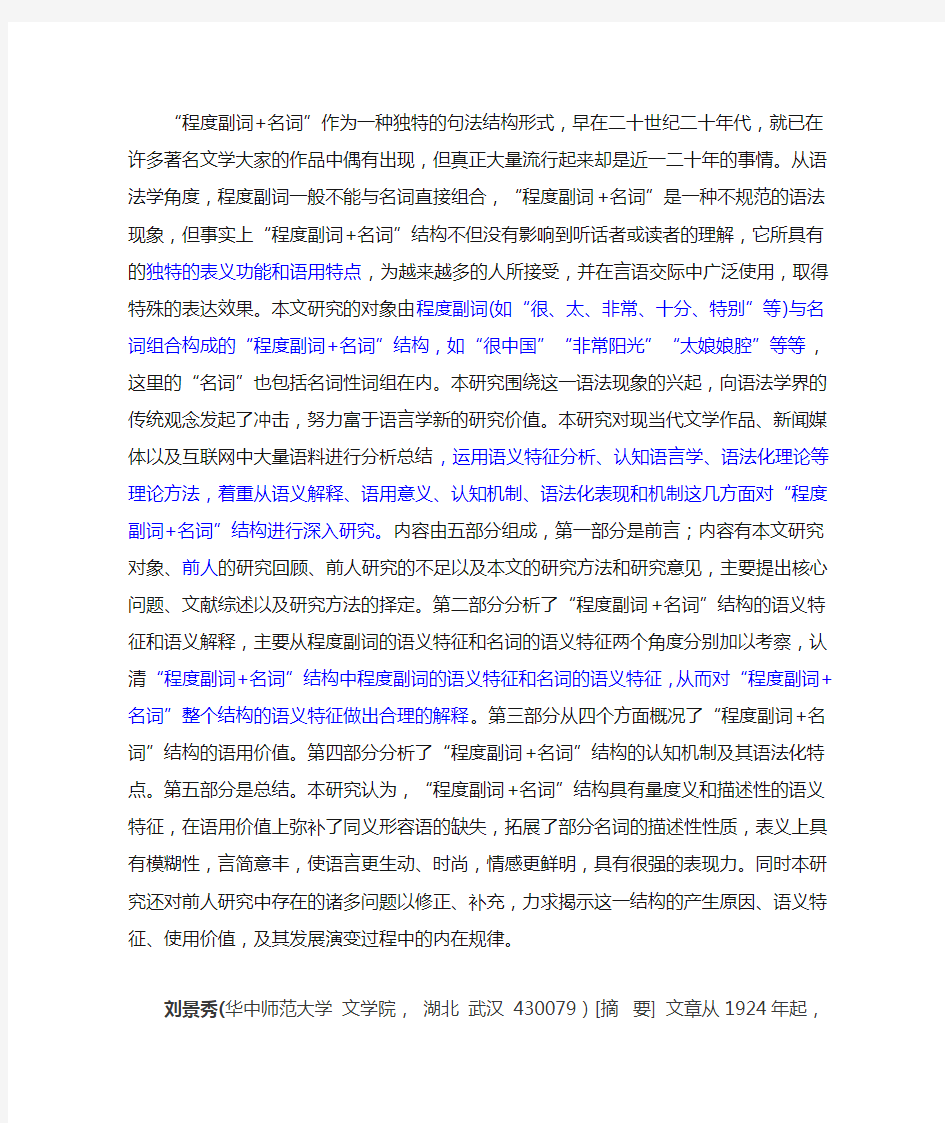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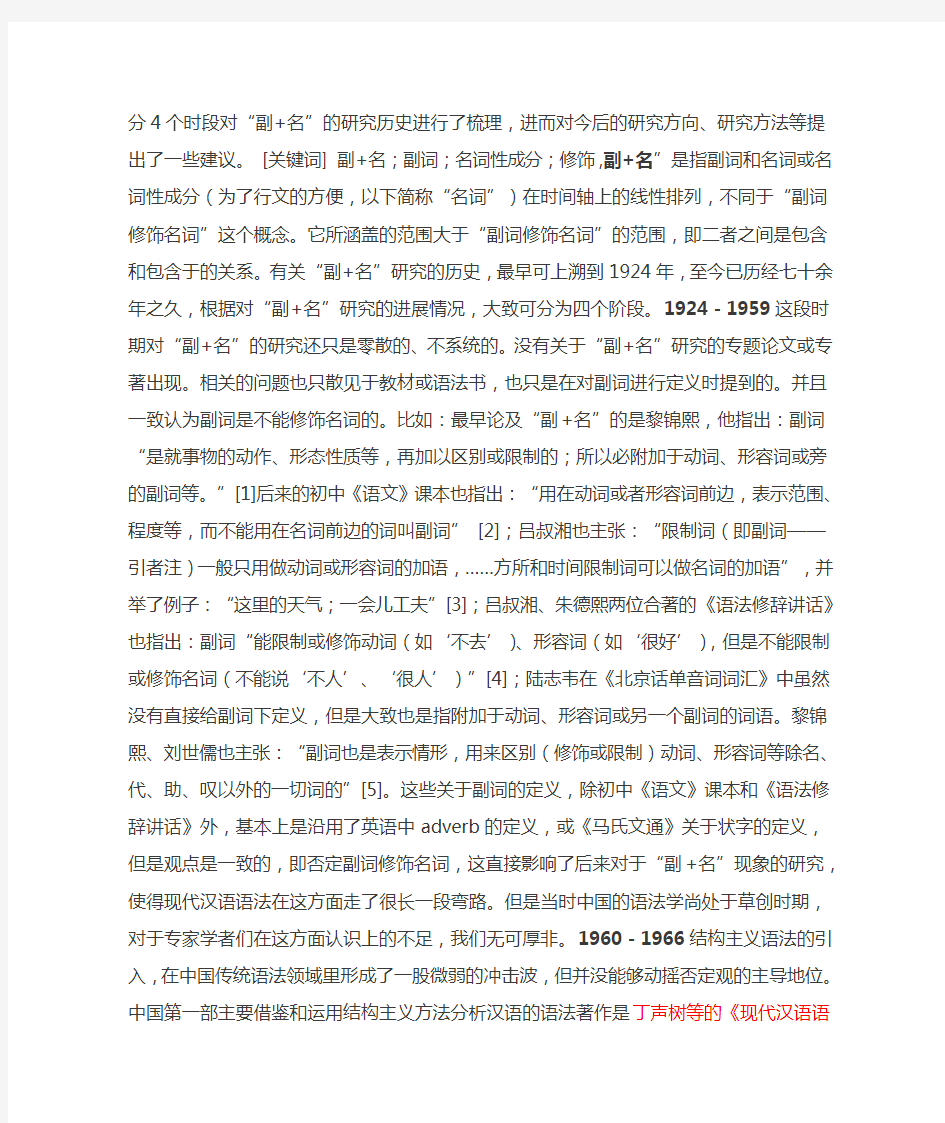
“程度副词+名词”作为一种独特的句法结构形式,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在许多著名文学大家的作品中偶有出现,但真正大量流行起来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从语法学角度,程度副词一般不能与名词直接组合,“程度副词+名词”是一种不规范的语法现象,但事实上“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不但没有影响到听话者或读者的理解,它所具有的独特的表义功能和语用特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在言语交际中广泛使用,取得特殊的表达效果。本文研究的对象由程度副词(如“很、太、非常、十分、特别”等)与名词组合构成的“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如“很中国”“非常阳光”“太娘娘腔”等等,这里的“名词”也包括名词性词组在内。本研究围绕这一语法现象的兴起,向语法学界的传统观念发起了冲击,努力富于语言学新的研究价值。本研究对现当代文学作品、新闻媒体以及互联网中大量语料进行分析总结,运用语义特征分析、认知语言学、语法化理论等理论方法,着重从语义解释、语用意义、认知机制、语法化表现和机制这几方面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进行深入研究。内容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前言;内容有本文研究对象、前人的研究回顾、前人研究的不足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意见,主要提出核心问题、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方法的择定。第二部分分析了“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语义特征和语义解释,主要从程度副词的语义特征和名词的语义特征两个角度分别加以考察,认清“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程度副词的语义特征和名词的语义特征,从而对“程度副词+名词”整个结构的语义特征做出合理的解释。第三部分从四个方面概况了“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语用价值。第四部分分析了“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认知机制及其语法化特点。第五部分是总结。本研究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具有量度义和描述性的语义特征,在语用价值上弥补了同义形容语的缺失,拓展了部分名词的
描述性性质,表义上具有模糊性,言简意丰,使语言更生动、时尚,情感更鲜明,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同时本研究还对前人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修正、补充,力求揭示这一结构的产生原因、语义特征、使用价值,及其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内在规律。
刘景秀(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摘要] 文章从1924年起,分4个时段对“副+名”的研究历史进行了梳理,进而对今后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提出了一
些建议。[关键词] 副+名;副词;名词性成分;修饰,副+名”是指副词和名词或名词性成分(为了行文的方便,以下简称“名词”)在时间轴上的线性排列,不同于“副词修饰名词”这个概念。它所涵盖的范围大于“副词修饰名词”的范围,即二者之间是包含和包含于的关系。有关“副+名”研究的历史,最早可上溯到1924年,至今已历经七十余年之久,根据对“副+名”研究的进展情况,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24-1959这段时期对“副+名”的研究还只是零散的、不系统的。没有关于“副+名”研究的专题论文或专著出现。相关的问题也只散见于教材或语法书,也只是在对副词进行定义时提到的。并且一致认为副词是不能修饰名词的。比如:最早论及“副+名”的是黎锦熙,他指出:副词“是就事物的动作、形态性质等,再加以区别或限制的;所以必附加于动词、形容词或旁的副词等。”[1]后来的初中《语文》课本也指出:“用在动词或者形容词前边,表示范围、程度等,而不能用在名词前边的词叫副词” [2];吕叔湘也主张:“限制词(即副词——引者注)一般只用做动词或形容词的加语,……方所和时间限制词可以做名词的加语”,并举了例子:“这里的天气;一会儿工夫”[3];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也指出:副词“能限制或修饰动词(如…不去?)、形容词(如…很好?),但是不能限制或修饰名词(不能说…不人?、…很人?)”[4];陆志韦在《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中虽然没有直接给副词下定义,但是大致也是指附加于动词、形容词或另一个副词的词语。黎锦熙、刘世儒也主张:“副词也是表示情形,用来区别(修饰或限制)动词、形容词等除名、代、助、叹以外的一切词的”[5]。这些关于副词的定义,除初中《语文》课本和《语法修辞讲话》外,基本上是沿用了英语中adverb的定义,或《马氏文通》关于状字的定义,但是观点是一致的,即否定副词修饰名词,这直接影响了后来对于“副+名”现象的研究,使得现代汉语语法在这方面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但是当时中国的语法学尚处于草创时期,对于专家学者们在这方面认识上的不足,我们无可厚非。1960-1966结构主义语法的引入,在中国传统语法领域里形成了一股微弱的冲击波,但并没能够动摇否定观的主导地位。中国第一部主要借鉴和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汉语的语法著作是丁声树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该著作虽然仍对副词能否修饰名词持否定态度,但已指出有特殊情况,并进行了简单分析:“副词通常不修饰体词,有几个副词可以这么用,大都跟数量或范围有关”。可是陆志韦却从构词法的角度分析了“最、仅、顶”等几个副词用在方位名词前的情况,并指出“副+名”是客观存在的,“副+名”的功能相当于名词;对于副词是否转化为形容词也没有作出肯定回答;对于“副+名”到底是词还是词组也只是提出了有商榷余地的看法,不过总体上还是倾向于是词组,即倾向于副词能修饰名词。这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有很大的偏差的,并且证据也不是很充分,多采用“大概、好像、不宜乎”等词语。这个时期出现了专门研究“副+名”的论文,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邢福义(1962),这篇论文是为了反驳张静(1961)的一些
观点而作的。张静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副词真不能修饰名词吗?我看能。……从数目上说,这绝不是…特殊?现象。”[6]并且举了很多的例子来说明。邢文针对张文“肯定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也是一般现象”这一观点,先排除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容易引起错觉的现象”[7],认为这些现象(即张文中的例子——引者注)中或者是名词为名形兼类,或者是副词修饰主谓短语,同时,指出了副词修饰名词现象的四种类型:副词+数量名结构;处所名词+副词+名词;时间名词+副词+时间名词;副词+方位名词,并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现象。我们认为,从数量上看,仅这四种类型已经不少了,再冠以“特殊”二字多少显得有点不太合适。朱德熙(1961)指出:“严格的副词,即符合下列两项标准的词:(1)能够修饰动词或形容词;(2)不能修饰名词,不能做主语、宾语、谓语。”不过,“其中有一部分可以修饰数量结构或…数·量·名?结构”,之所以不把副词修饰数量结构或数量名结构的现象看作是副词修饰名词现象,是因为“这就跟我们说的副词不能修饰名词有矛盾”[8]。这样看来,人们当时已经注意到了有与既定的副词的定义相冲突的现象,但人们并没有客观地对待它,而是被动地去修订那个定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既定的观念、理论对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多少时有点桎梏之嫌。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很多学科的发展都处于停滞状态,语言学的发展也不例外,这段时期的语言学界曾一度陷入沉默,但是,语言学者们并没有停止耕耘,他们等待的是厚积而薄发,改革开放就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1978-1989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沉寂许久的中国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万物复苏,语言学也借着这股春风开始蓬勃发展。对“副+名”的研究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这个时期专门研究“副+名”的文章并不是很多,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肯定说,即对“副词修饰名词”持肯定态度。如马真(1981)一文专门讨论了副词修饰数量词的现象,对于能够修饰数量词的40多个副词进行了分类,并做了系统的考察,指出修饰数量词的副词主要表达七种意义:言够、言少、言多、等量、估量、
实量、总计[9]。李珠(1980)指出:“有一些副词可以直接修饰数量词语”[10] ,如“想去看
比赛的就一个人”,而对于放在主语前面的副词,作者认为是副词“修饰主谓短语(小句)”,如“大概他不会来了。”滕安利(1982)运用类比的方法分析指出,诸如“就厂长没走”之类的“范围副词+名词性主语+谓语”的结构,范围副词,尤其是“特指部分的范围副词,如只、仅、就、光、单、单单、仅仅、唯独、大凡等等可以修饰名词、代词、名词性词组。”[11] 另外,柴世森(1980)对副词“最”进行了个案考察,得出了“说副词不能修饰名词,就值得讨论了。…最?就能修饰某些名词”[12]的结论,还对“最”能够修饰名词进行了分类,主要有:大部分的方位名词、一些抽象名词、一些具体名词。(2)否定观。持否定观的学者多是采用“词类转化说”来解释这种现象。如吕叔湘(1989)认为:在“真的,小颜,有时候你太感情了。”这样的程度副词+名词的结构里,是“把别的词类当形容词用”[13]了。方华(1986)回顾了以往的研究状况,并运用词类范畴的历史性解释“副+名”现象,认为这里或者是副词转化成了语气词、连接词,或者是名词已经不再是名词,而是转化成了形容词。除了上述两个方面外,这个时期还有一篇文章非常值得重视——李一平(1983),该文章没有对副词能否修饰名词发表见解,而是考察了“副+名”的分布环境和限制条件,主要有四种情况:副词位于做谓语的名词性成分之前;副词位于做宾语的名词性成分之前;副词位于做状语的名词性成分之前;副词位于做主语的名词性成分之前,并指出,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大部分都出现在句子环境里,即副词修饰名词并不是完全自由的[14]。长期以来,对于“副+名”现象人们只关注副词可不可以修饰名词这一点上,并且尚未得出一致结论,这篇文章的发表,为我们的研究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子,拓宽了研究思路。总的来说,由于受到文革的重创,人们的知识结构尚
未恢复,这个时期的“副+名”研究仍存在着深度不够,流于表面的现象。1990-20031990年前后,国内外各种语法理论蜂起,国外如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国内如朱德熙的词组本位语法体系,胡裕树、范晓提出的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邢福义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出的大三角(普通话、方言、古汉语)和小三角(语表、语里、语值)的两个三角理论,等等。这些新的理论的提出为我们的语法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使新时期的语法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开始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汉语语法研究。相应地,“副+名”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局面。新时期的“副+名”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副词不能修饰名词;一是副词能修饰名词;再一个是副名为什么能组合。(一)副词不能修饰名词一部分学者认为副词是绝对不能修饰名词的,并对“副+名”进行了解释,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
的理论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也各不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词类活用说:胡明扬(1992)指出:类似“很青春”这样的说法,“只能算是临时的…活用?,是名词临时活用作形容词”[15]。邹韶华(1990)也认为:“副+名”结构里的名词虽然经常以名词的身份出现,但是偶尔会用作形容词或者具备了形容词的部分语法特征,亦即名词形化。持这种观点的还有李泉(2002)。(2)动词省略说:于根元(1991)一文就指出:“副+名的情况不是单一的”[16],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动词“不露面”而造成的,如“很有气派”→“很气派”。陈一民(1999)也认为名词前的副词有一部分就是修饰隐含的动词的。张国安(1995)也指出:“副+名”作谓语时是省略了动词,副词修饰的是省略的动词。笔者以为:如果动词省略说成立的话,就意味着汉语中不存在名
词性谓语句,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汉语中名词性谓语句,这种观点将导致整个语法体系的重构,而事实上这是无法想象的。(3)修辞说:山述兰(2003)认为这个结构是“一种突破语法规范的修辞现象”[17],属于转类的修辞方法。于根元(1991)也认为:一部分“副+名”是“临时的修辞用法”,如“最感情”“太瘪三”,“临时的修辞用法用多
了,就容易固定,人们会以为是普通的用法”。(4)修饰主谓短语说:陈一民(1999)认为“副+名”处于主语位置时时修饰“句子成分(即主谓结构——引者注)”[18]的。与90年代以前的否定观相比,新时期的否定观更加注重对事实的考察和理论上的分析。相关文章的可读性有所增强。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副+名”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二)副词能修饰名词进入
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持肯定态度,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结构的句法特征、语义限制、语用价值进行了分析。总的来说,在分析这一结构时,人们主要采用的理论是三个平面理论,比如:原新梅(1996)运用三个平面语法理论对该结构的语义特点、语法功能、修辞功效及选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归纳;鲜丽霞(2001)也是运用三个平面理论对“程度副词+名词”作了分析,并探讨了这一结构的潜性和显性特征。还有徐彬、付光宇(2003)、尹琪(2002)等等。有的从语义角度分析了“副+名”的语义上的限制条件。如李敏(2003)讨论了名词与程度副词组合的语义上的限制条件,进入这个结构的名词必须是以下几类:方位义名词、包含形素的名词、蕴涵“量度”义的名词、“标准”义名词、“类别”义名词、“特质”义专有名词、专业术语类名词。还有用别的理论进行分析的,如王晓莘、张舸(1998)就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对该现象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解释。还有的只是在论述别的问题时附带提及的。还有对“副+名”进行全面分析的,如王素梅(1996),把“副+名”进行了归类分析,得出了“副词可以修饰名词”的结论,这一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副+名”现象。还有一些文章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如史锡尧(1994)强调把“副+名”放入句子中来考察,这样,很容易得出副词可以修饰名词的结论。周建云(2003)对副词修饰名词(即“程度副词+名词”和“比N还N”格式)的方式、条件、特点及归属进行了分析考察,认为“副词修饰名词这种语言现象,正是汉语随着社会发展而主动应答积极调适的反映,也是汉语使用者不断创造求新约定俗成的结果”。“对副名组合这一新型短语,既没有必要用传统的语法理论去衡量其合法与否,也没有必要
牵强附会地解释为名词活用为形容词/动词。”[19]杨霞林(2003)则一方面承认否定副词+名词是省略了动词的现象,但是另一方面又肯定否定副词是修饰名词的,它和程度副词+名词的现象即使说是特殊的,也是一种接近于普遍的特殊。岳东升(1995)则认为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是一种语法变异。(三)“副+名”为什么能够组合对“副+名”进行解释的角度有很
多,其中以从语义角度进行解释的居多,其着眼点都是名词的语义特征。如施春宏(2001)从名词的语义特征角度探讨了“副+名”的可能性的问题,认为名词的描述性语义特征是副名组合显现的客观依据。谭景春(1998)则认为“副+名”的显现是源于性质义强的名词向形容词转换。张谊生(1996,1997)认为进入“副+名”结构的名词必须具有这些语义特征:顺序义、类别义、量度义、动核化、性状义。肖奚强(2001)则运用内涵义解释了程度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储泽祥、刘街生(1997)认为“副+名”组合的基础是名词的性质细节的再次“显现”。其他的还有,如从语法功能角度进行解释的,如张伯江(1994)“副+名”的出现是由于该结构中的名词发生了功能游移,名词丢掉了一些名词的语法特征而临时具备了形容词的一些语法功能;从语用角度进行解释的,如桂诗春(1995)就从语用角度出发,把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归结为人们使用语言的策略性行为;从文化角度进行解释的,如邢福义(1997)虽然强调“很X”结构槽是“很淑女”之类说法产生的语言背景,但是更强调的是该类说法产生的文化背景,即具有特定的文化修养的人对于物体属性的“异质感受”,就是这特定的文化背景促成了该类说法的发展;从修辞学的
角度进行解释也是一个很新的角度,如邱凌(2002)从修饰学上的浅显理论出发,认为“程度副词+N”的产生是由于该结构中的名词的潜在的意义、潜性功能及潜性效果的显性化等等。总之,新时期对于“副+名”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有具体分析,有系统考察,也有理论阐释,研究的角度不断变化,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加强。结语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几十年来,我国语言学界对“副+名”研究的成果还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不足。笔者以为,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加注意下面几个方面:(1)鉴于以往对“副+名”的缺乏全面系统的考察,以后可以对“副+名”现象进行系统考察,以求对该结构有更深层的观察。(2)加强演变研究。施春宏(2001)提到过一点,但是没有作详细的分析考察。(3)可进行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普通话和方言之间是相互影响的,通过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比较,对于“副+名”的缘起也许会有一个更深的了解。(4)进行跨语言比较研究。立足人类语言的共性来考察其他的语言,使该结构能够为普通语言学、语言类型学提供研究的参考文献。据笔者观察,英语、日语、德语等语言中,也有类似于汉语中的“副+名”的现象,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