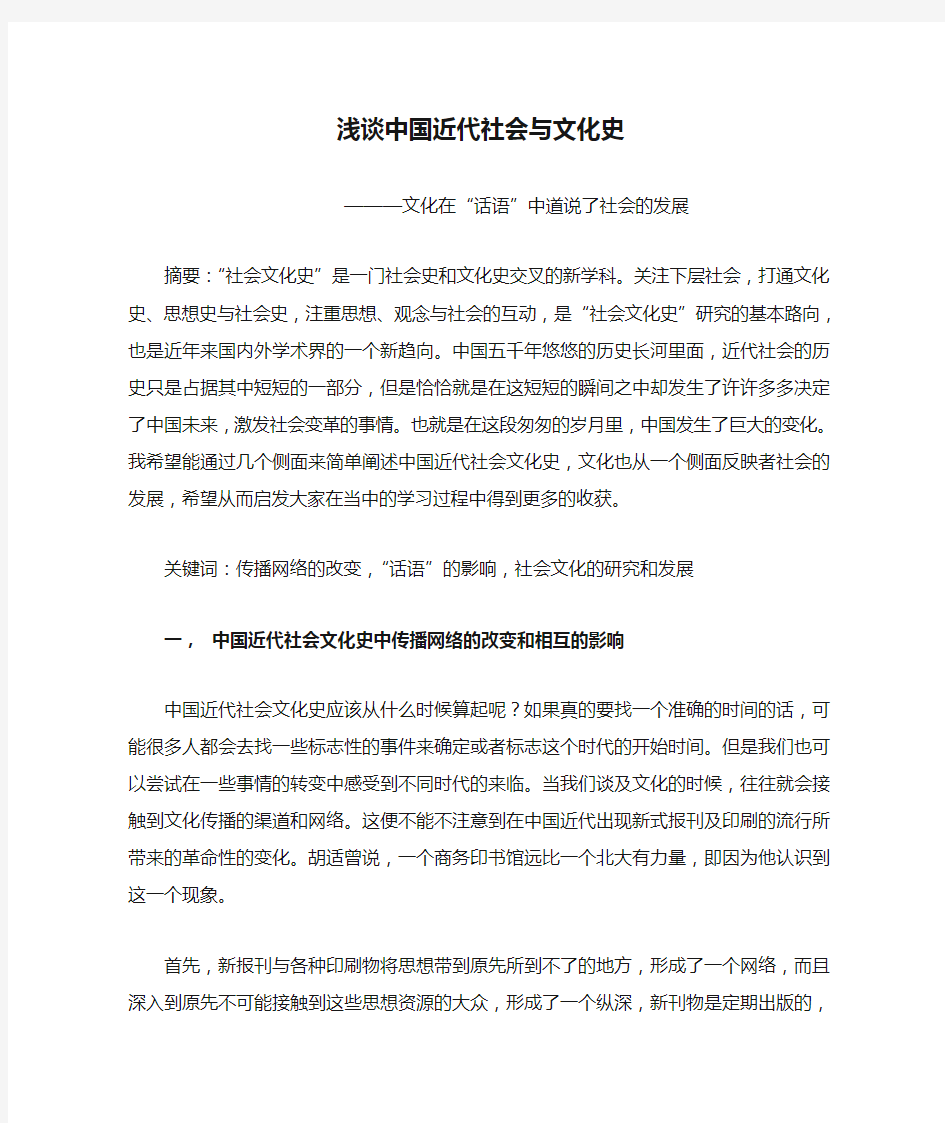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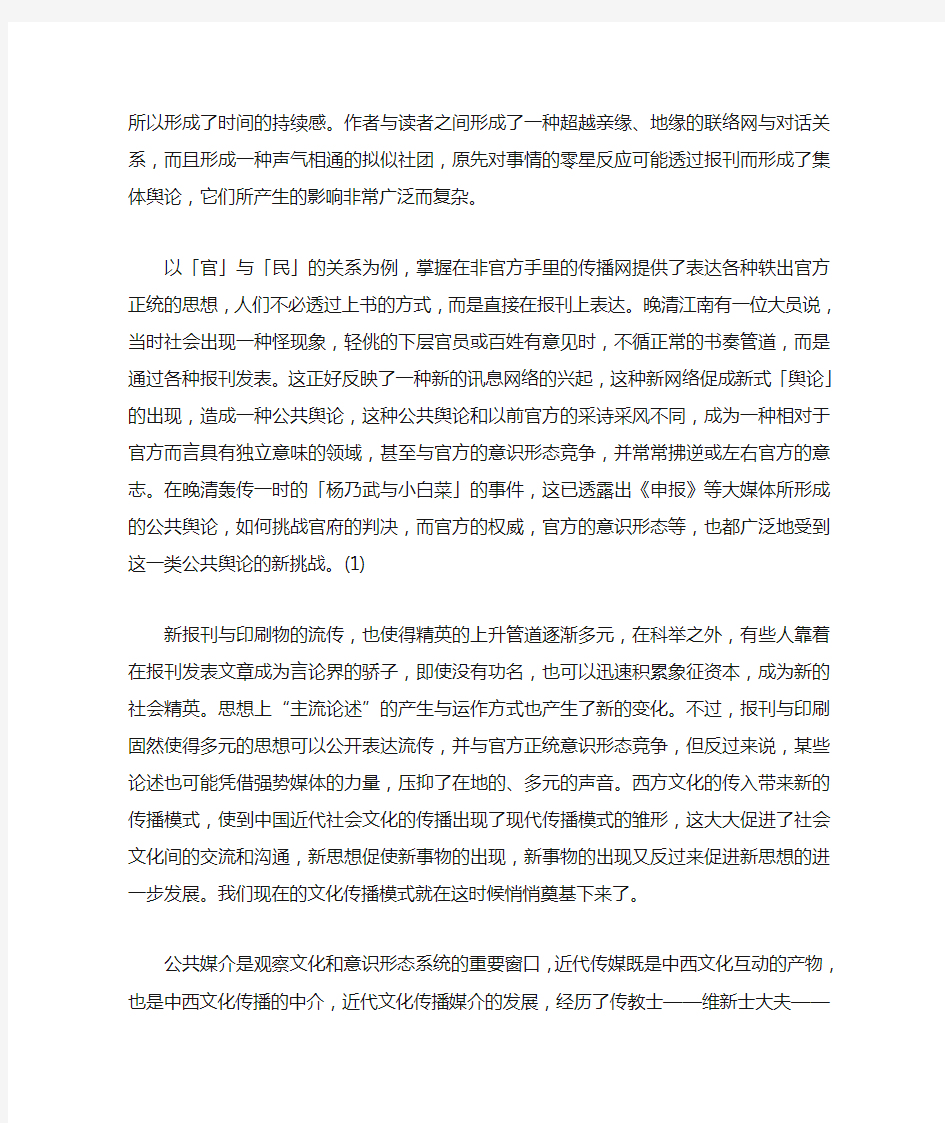
浅谈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
———文化在“话语”中道说了社会的发展
摘要:“社会文化史”是一门社会史和文化史交叉的新学科。关注下层社会,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也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新趋向。中国五千年悠悠的历史长河里面,近代社会的历史只是占据其中短短的一部分,但是恰恰就是在这短短的瞬间之中却发生了许许多多决定了中国未来,激发社会变革的事情。也就是在这段匆匆的岁月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希望能通过几个侧面来简单阐述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文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者社会的发展,希望从而启发大家在当中的学习过程中得到更多的收获。
关键词:传播网络的改变,“话语”的影响,社会文化的研究和发展
一,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中传播网络的改变和相互的影响
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如果真的要找一个准确的时间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去找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来确定或者标志这个时代的开始时间。但是我们也可以尝试在一些事情的转变中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来临。当我们谈及文化的时候,往往就会接触到文化传播的渠道和网络。这便不能不注意到在中
国近代出现新式报刊及印刷的流行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胡适曾说,一个商务印书馆远比一个北大有力量,即因为他认识到这一个现象。
首先,新报刊与各种印刷物将思想带到原先所到不了的地方,形成了一个网络,而且深入到原先不可能接触到这些思想资源的大众,形成了一个纵深,新刊物是定期出版的,所以形成了时间的持续感。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亲缘、地缘的联络网与对话关系,而且形成一种声气相通的拟似社团,原先对事情的零星反应可能透过报刊而形成了集体舆论,它们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广泛而复杂。
以「官」与「民」的关系为例,掌握在非官方手里的传播网提供了表达各种轶出官方正统的思想,人们不必透过上书的方式,而是直接在报刊上表达。晚清江南有一位大员说,当时社会出现一种怪现象,轻佻的下层官员或百姓有意见时,不循正常的书奏管道,而是通过各种报刊发表。这正好反映了一种新的讯息网络的兴起,这种新网络促成新式「舆论」的出现,造成一种公共舆论,这种公共舆论和以前官方的采诗采风不同,成为一种相对于官方而言具有独立意味的领域,甚至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竞争,并常常拂逆或左右官方的意志。在晚清轰传一时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事件,这已透露出《申报》等大媒体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如何挑战官府的判决,而官方的权威,官方的意识形态等,也都广泛地受到这一类公共舆论的新挑战。(1)
新报刊与印刷物的流传,也使得精英的上升管道逐渐多元,在科举之外,有些人靠着在报刊发表文章成为言论界的骄子,即使没有功名,也可以迅速积累象征
资本,成为新的社会精英。思想上“主流论述”的产生与运作方式也产生了新的变化。不过,报刊与印刷固然使得多元的思想可以公开表达流传,并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竞争,但反过来说,某些论述也可能凭借强势媒体的力量,压抑了在地的、多元的声音。西方文化的传入带来新的传播模式,使到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传播出现了现代传播模式的雏形,这大大促进了社会文化间的交流和沟通,新思想促使新事物的出现,新事物的出现又反过来促进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现在的文化传播模式就在这时候悄悄奠基下来了。
公共媒介是观察文化和意识形态系统的重要窗口,近代传媒既是中西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传播的中介,近代文化传播媒介的发展,经历了传教士——维新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过程。祝兴平认为,近代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大众化、世俗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使得文化传播从特权阶层解放出来,出现了民间化的特点。文本创造者身份的普泛化、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文化接受的大众化,是前所未有的变革。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新式学堂的崛起、域外科学和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传播,造就了一个新的知识群体,客观上构成了对旧的政治体制和封建文化的批判力量和破坏性因素。伴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白话媒体空前活跃,反映了大众化、平民化、社会化的价值取向,打破了封建正统文化、精英文化的传统,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2)
二,从“话语”中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改变
中国的近代社会是一个动荡的社会,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在这个时候开始摇摇欲坠,西方诸国列强的入侵带来崭新的西方文化,刺激了当时人们的思想也引发新的思潮。但是封建王朝并不想轻易地放手而去,他们依然希望通过传统的封建思想让中国依然统治在他们的脚下。因此在这样一个半封建本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下,在东方传统思想和西方先进相互碰击中,中国的近代文化出现和其他国家所不同的斑斓色彩。这些“色彩”在很多“平凡”的地方也展现了出来。我们即使从当时的话语的转变中也能找到这种社会文化的转变。
“话语”一词的流行,源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语言学转向”;事实上,从一开始,它又超越了语言学本身。在传统语言学中,“话语”通常被视为一种规则明确、意涵清晰而确定的言说。或者通俗地说是人们对某事物的表达方式或者定义方式。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社会里,人们在写作,交流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表达方式的转变的这个侧面看到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变化。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在封建主义的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交融中,传统的中国言语文化也悄悄出现了变化。在这方面,美国汉学家艾尔曼(Benjamin A.Elman)的有关研究具有典型的先行性代表意义。艾尔曼是较早将“话语”理论有选择地明确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并对中国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书中,他借鉴了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理论和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阐发的‘话语’理论”。他认为“考据学就是一种话语,一种学术性谱系和意义……作为思想学术事件,实证性朴学话语特点的形成是基本学术观念变化的反映。后者同时还引发
了对传统认知和理解的更重大的基本变革”。(2) 艾尔曼把从理学到朴学的转换既可以看作为一种儒学范式的转换,也视为一种儒学话语的转换——一种“从道德主义话语转向知识主义话语”、“追求客观性的思潮压倒内圣理想”的革命。由此出发,他揭示了朴学“话语”执著于“考据”和“实证”,重视知识的累积性和客观性,显出专业化和职业化等特征。认为在“话语”载体上,这种变化体现为“札记体”取代“语录体”成为时尚,在内容上体现为史学地位大幅上升,诸子学、算学、历学等开始复兴,在经学内部,则表现为“四书”地位降低,“五经”地位上扬等特点。他还把当时江南地区的出版业、藏书楼、书院、商业发展、官方与商人的学术赞助、学人之间的交流网络等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所谓“江南学术共同体”等内容纳入分析的视野,从而使其所谓“一种居主流地位的学术话语要为另一种所取代,取决于众多社会和学术因素的相互作用”的断言,(3) 令人信服地落到了实处。他的论述揭示了近代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出现的变化。
在《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一书中,艾尔曼的这种研究方法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他称传统思想史研究为“哲学”式的观念史路数(重观念的“内在理路”),而把思想史和社会史、政治史糅合在一起的路数,归之为“(新)文化史”。(4) 从而可以看出,在学人的推动之下,新的思想在寂静中慢慢地改变着旧有的思想和文化。话语的表达方式从“哲学”的就观念逐渐转变为重视史学的“文化史”的转变。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同样运用此种话语分析方法对中国文化的改变进行了阐述。其中该书下卷第2部《科学话语共同体》,把近代中国“科学”观念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