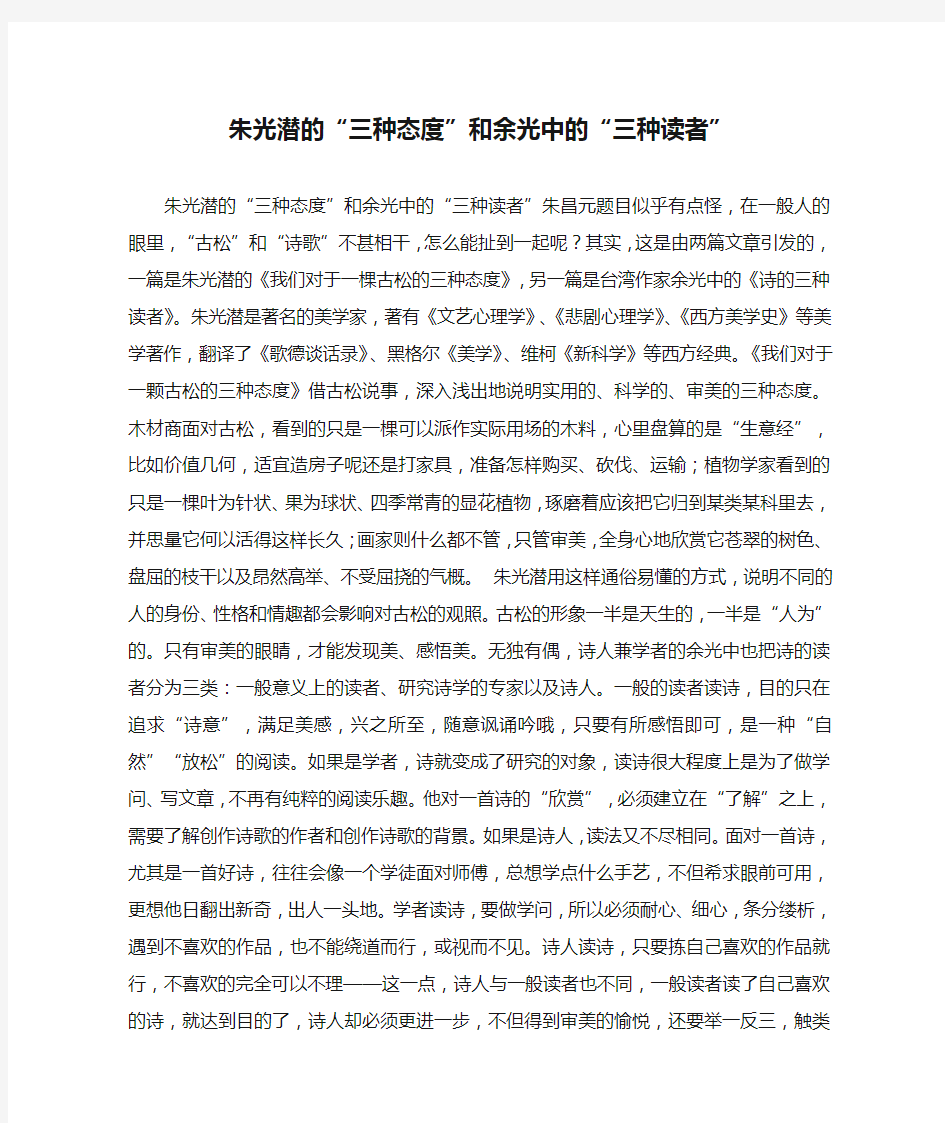

朱光潜的“三种态度”和余光中的“三种读者”
朱光潜的“三种态度”和余光中的“三种读者”朱昌元题目似乎有点怪,在一般人的眼里,“古松”和“诗歌”不甚相干,怎么能扯到一起呢?其实,这是由两篇文章引发的,一篇是朱光潜的《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另一篇是台湾作家余光中的《诗的三种读者》。朱光潜是著名的美学家,著有《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西方美学史》等美学著作,翻译了《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美学》、维柯《新科学》等西方经典。《我们对于一颗古松的三种态度》借古松说事,深入浅出地说明实用的、科学的、审美的三种态度。木材商面对古松,看到的只是一棵可以派作实际用场的木料,心里盘算的是“生意经”,比如价值几何,适宜造房子呢还是打家具,准备怎样购买、砍伐、运输;植物学家看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琢磨着应该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并思量它何以活得这样长久;画家则什么都不管,只管审美,全身心地欣赏它苍翠的树色、盘屈的枝干以及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朱光潜用这样通俗易懂的方式,说明不同的人的身份、性格和情趣都会影响对古松的观照。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是“人为”的。只有审美的眼睛,才能发现美、感悟美。无独有偶,诗人兼学者的余光中也把诗的读者分为三类:一般意义上的读者、研究诗学的专家以及诗人。一般的读者读诗,目的只在追求“诗意”,满足美感,兴之所至,随意讽诵吟哦,只要有所感悟即可,是一种“自然”“放松”的阅读。如果是学者,诗就变成了研究的对象,读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做学问、写文章,不再有纯粹的阅读乐趣。他对一首诗的“欣赏”,必须建立在“了解”之上,需要了解创作诗歌的作者和创作诗歌的背景。如果是诗人,读法又不尽相同。面对一首诗,尤其是一首好诗,往往会像一个学徒面对师傅,总想学点什么手艺,不但希求眼前可用,更想他日翻出新奇,出人一头地。学者读诗,要做学问,所以必须耐心、细心,条分缕析,遇到不喜欢的作品,也不能绕道而行,或视而不见。诗人读诗,只要拣自己喜欢的作品就行,不喜欢的完全可以不理——这一点,诗人与一般读者也不同,一般读者读了自己喜欢的诗,就达到目的了,诗人却必须更进一步,不但得到审美的愉悦,还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善加借鉴。余光中说“譬如食物,一般读者但求可口,诗人于可口之外,更须注意摄取营养”。比如苏东坡,很喜欢“前辈”大诗人陶渊明,熟读陶诗,便作了许多“和陶诗”。苏轼诗集中,和韵次韵的作品,竟占了五分之一以上,那首有名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也是为“和”自己的弟弟苏辙的作品而作,而后者的原作却没有多少人记得了。“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强调诗人要打开眼界,多读各家作品,才能找到自己要走的大道。“读者读诗,有如初恋;学者读诗,有如选美;诗人读诗,有如择妻。读者赏花。学者摘花。诗人采蜜。”余光中的比喻生动、风趣,耐人寻味。朱光潜的“三种态度”和余光中的“三种读者”不约而同,都在强调即使面对相同的作品,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眼光,采取不同的读法,收获各自的审美体验和人生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