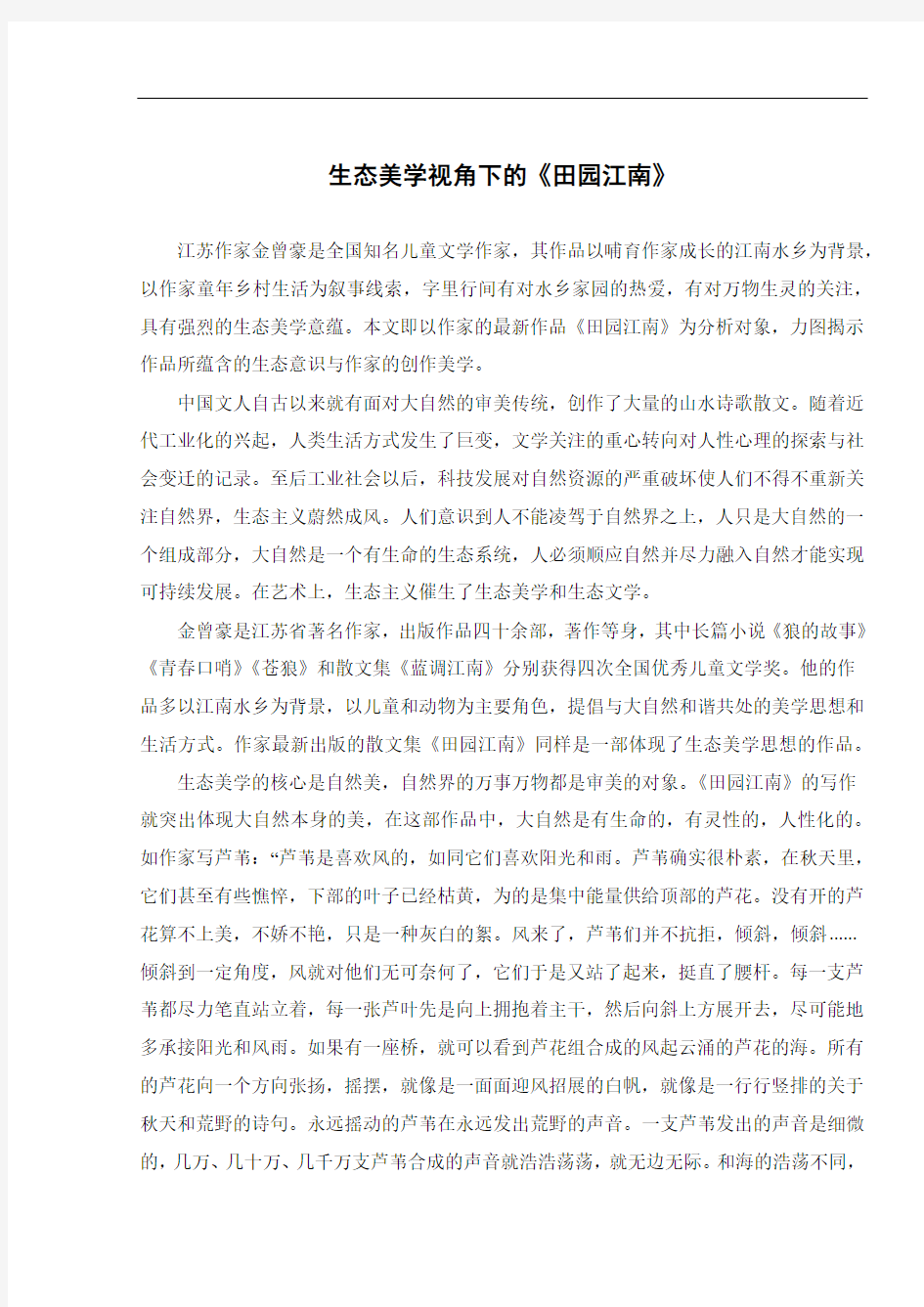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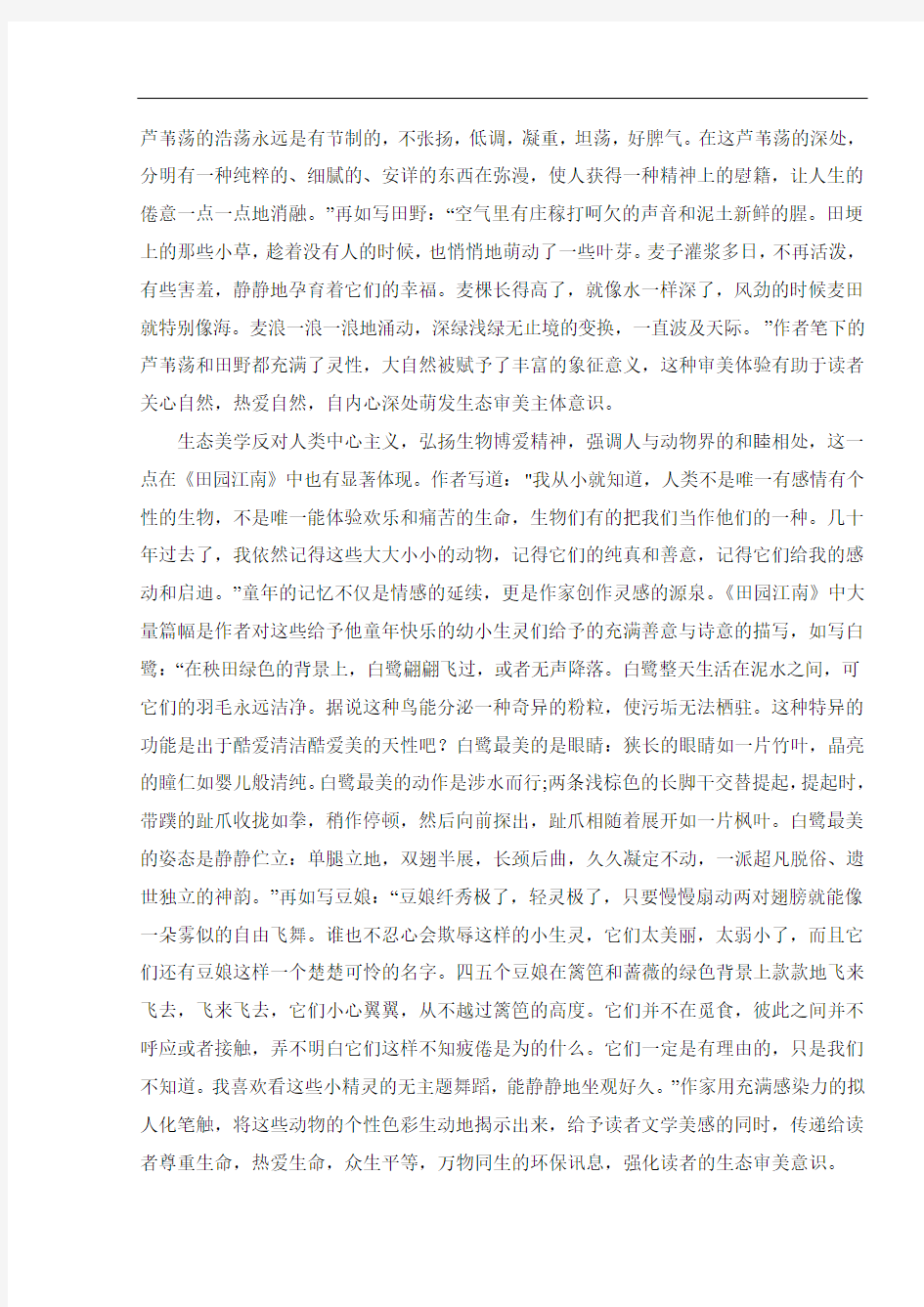
生态美学视角下的《田园江南》
江苏作家金曾豪是全国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其作品以哺育作家成长的江南水乡为背景,以作家童年乡村生活为叙事线索,字里行间有对水乡家园的热爱,有对万物生灵的关注,具有强烈的生态美学意蕴。本文即以作家的最新作品《田园江南》为分析对象,力图揭示作品所蕴含的生态意识与作家的创作美学。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有面对大自然的审美传统,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歌散文。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兴起,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文学关注的重心转向对人性心理的探索与社会变迁的记录。至后工业社会以后,科技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关注自然界,生态主义蔚然成风。人们意识到人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人只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大自然是一个有生命的生态系统,人必须顺应自然并尽力融入自然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艺术上,生态主义催生了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学。
金曾豪是江苏省著名作家,出版作品四十余部,著作等身,其中长篇小说《狼的故事》《青春口哨》《苍狼》和散文集《蓝调江南》分别获得四次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他的作
品多以江南水乡为背景,以儿童和动物为主要角色,提倡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学思想和生活方式。作家最新出版的散文集《田园江南》同样是一部体现了生态美学思想的作品。
生态美学的核心是自然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审美的对象。《田园江南》的写作
就突出体现大自然本身的美,在这部作品中,大自然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人性化的。如作家写芦苇:“芦苇是喜欢风的,如同它们喜欢阳光和雨。芦苇确实很朴素,在秋天里,它们甚至有些憔悴,下部的叶子已经枯黄,为的是集中能量供给顶部的芦花。没有开的芦花算不上美,不娇不艳,只是一种灰白的絮。风来了,芦苇们并不抗拒,倾斜,倾斜......
倾斜到一定角度,风就对他们无可奈何了,它们于是又站了起来,挺直了腰杆。每一支芦苇都尽力笔直站立着,每一张芦叶先是向上拥抱着主干,然后向斜上方展开去,尽可能地多承接阳光和风雨。如果有一座桥,就可以看到芦花组合成的风起云涌的芦花的海。所有的芦花向一个方向张扬,摇摆,就像是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白帆,就像是一行行竖排的关于秋天和荒野的诗句。永远摇动的芦苇在永远发出荒野的声音。一支芦苇发出的声音是细微的,几万、几十万、几千万支芦苇合成的声音就浩浩荡荡,就无边无际。和海的浩荡不同,
芦苇荡的浩荡永远是有节制的,不张扬,低调,凝重,坦荡,好脾气。在这芦苇荡的深处,分明有一种纯粹的、细腻的、安详的东西在弥漫,使人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慰籍,让人生的倦意一点一点地消融。”再如写田野:“空气里有庄稼打呵欠的声音和泥土新鲜的腥。田埂上的那些小草,趁着没有人的时候,也悄悄地萌动了一些叶芽。麦子灌浆多日,不再活泼,有些害羞,静静地孕育着它们的幸福。麦棵长得高了,就像水一样深了,风劲的时候麦田就特别像海。麦浪一浪一浪地涌动,深绿浅绿无止境的变换,一直波及天际。”作者笔下的芦苇荡和田野都充满了灵性,大自然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这种审美体验有助于读者关心自然,热爱自然,自内心深处萌发生态审美主体意识。
生态美学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弘扬生物博爱精神,强调人与动物界的和睦相处,这一点在《田园江南》中也有显著体现。作者写道:"我从小就知道,人类不是唯一有感情有个性的生物,不是唯一能体验欢乐和痛苦的生命,生物们有的把我们当作他们的一种。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这些大大小小的动物,记得它们的纯真和善意,记得它们给我的感动和启迪。”童年的记忆不仅是情感的延续,更是作家创作灵感的源泉。《田园江南》中大量篇幅是作者对这些给予他童年快乐的幼小生灵们给予的充满善意与诗意的描写,如写白鹭:“在秧田绿色的背景上,白鹭翩翩飞过,或者无声降落。白鹭整天生活在泥水之间,可它们的羽毛永远洁净。据说这种鸟能分泌一种奇异的粉粒,使污垢无法栖驻。这种特异的功能是出于酷爱清洁酷爱美的天性吧?白鹭最美的是眼睛:狭长的眼睛如一片竹叶,晶亮的瞳仁如婴儿般清纯。白鹭最美的动作是涉水而行;两条浅棕色的长脚干交替提起,提起时,带蹼的趾爪收拢如拳,稍作停顿,然后向前探出,趾爪相随着展开如一片枫叶。白鹭最美的姿态是静静伫立:单腿立地,双翅半展,长颈后曲,久久凝定不动,一派超凡脱俗、遗世独立的神韵。”再如写豆娘:“豆娘纤秀极了,轻灵极了,只要慢慢扇动两对翅膀就能像一朵雾似的自由飞舞。谁也不忍心会欺辱这样的小生灵,它们太美丽,太弱小了,而且它们还有豆娘这样一个楚楚可怜的名字。四五个豆娘在篱笆和蔷薇的绿色背景上款款地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它们小心翼翼,从不越过篱笆的高度。它们并不在觅食,彼此之间并不呼应或者接触,弄不明白它们这样不知疲倦是为的什么。它们一定是有理由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我喜欢看这些小精灵的无主题舞蹈,能静静地坐观好久。”作家用充满感染力的拟人化笔触,将这些动物的个性色彩生动地揭示出来,给予读者文学美感的同时,传递给读者尊重生命,热爱生命,众生平等,万物同生的环保讯息,强化读者的生态审美意识。
生态美学的目标,是审美主体通过审美活动,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敬畏自然、爱护自然,并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中获得内心的宁静与满足。生态美学强调“平等”与“和谐”的主体审美态度在《田园江南》的文字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如作者写水乡清晨:“布谷鸟来到江南时,正是初夏。农家大多新换了蒲草编的席子,清香。布谷鸟常常进入我初夏的梦境,一声又一声,然后我就醒了。醒了我也不睁开眼睛,伸展四肢,让身体尽量多地接触席子;侧过头,吸吮蒲草水幽幽的清香……就觉得世界很太平,很干净,很美妙;觉得自己
很年轻,很健康,很英俊。”写田野里的泥土:“泥土记不清它曾经长多少茬庄稼了,也记不清养活过多少辈的人了。一切生命从泥土出发,又回归于泥土。生命不过是泥土的现世……不要过多少日子,田埂又会生出许许多多顽强的草和美丽的花。草丛里还会出现蝈蝈、蟋蟀、油呤、蚱蜢、西瓜虫、萤火虫……你走过田埂,蚱蜢像水一样飞溅起来,蝈蝈赶忙假装成草叶,蟋蟀像侠客一般神出鬼没……赤脚走在田埂上,只要细心体会,你就会发现,每走一步,脚底的感触都是不尽相同的。你感觉到了脚底下泥土的质地——它的韧性,它的温情,它的无限的可塑性和生命力。泥土是大自然的肌肤,赤脚走在田埂上,我们和大地肌肤相亲,就接通了与大自然的原始联系。”这些具有感染力的文字显示出作者在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中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与力量,体现出精神生态和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这部作品读来不仅净化读者心灵,也在维护人的精神世界平衡和自然界生态平衡方面显示出智慧与美丽的光芒。
生态美学强调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并非轻视人类的社会行为。相反,生态美学关注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关注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生态美学是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基础,并涉及到人与自身、人与社会多个层面的动态平衡,从生态美学的观点看,与自然和谐的乡村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家园。金曾豪在《田园江南》中,对童年时期的乡村社会有强烈的怀旧之情。他写道:我的童年是在乡村度过的,那是我一生的福分。书中大部分篇幅来自对童年生活的回忆:童年时,金曾豪也有过自己的百草园,那里也有低唱的油蛉和弹琴的蟋蟀。村里的高家竹园和朱家墓园是孩子们亲近自然的乐园,他们在这里看蜘蛛结网,逮麻雀,赛乌龟,下斗兽棋,唱评弹。夏夜,孩子们下河泡澡,追逐鸭群,在河岸上捉萤火虫,充分享受田园生活的乐趣。他也有一间三味书屋,善良的大姑妈用自己的言传身教,以故事浇灌幼小的心田,把平和、宁静的气质植入他的性格中。小镇上每个人都认识,日常生活充满了情趣。作家通过对故乡美景和敦厚民风的温馨回忆,传
递给读者乡村生活的和谐之美。同时他也不无忧虑地写到:人们正在努力地改变乡村,许多美妙的乡村风土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淡出。发展和修改也许是必须的,但那一定应当是有理有节的,否则,我们就会看不到我们的乡愁,找不到回家的路。
金曾豪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到自己作品的创作动机:“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日出的瑰丽、海涛的恢弘、瀑布的激越、虎啸的雄悍、鹤唳的悲怆、秋虫的幽远……离开了如此丰富,生动的感染,人的情感将会怎样的苍白和干癟!可当今的孩子们却被种种的原因与大自然阻隔着、疏远着。儿童文学是最接近大自然的文学。向孩子展示美妙神奇的大自然,实在是儿童文学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与田园的沟通和亲近,能使人的人心开阔,能使人的精神清洁。在素朴健壮的田园劳作和生活,人会情不自禁地怀有美好的心意。在平凡的乡村生活中,很容易就能读出来质朴而温婉、平和而深邃的人间情怀,乡村原是人类与大自然共同创造的,不仅有造化神奇的自然环境,也有人与生物和谐共处的人文环境。生产了丰厚的物质,培育了温婉、精致富有审美情趣的江南文化的生态图景,就是作者所意图展现和保留记录下来的。可见,作者是有意识将生态美学观点贯彻在《田园江南》的写作之中,而这部作品也确实实现了这一美学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