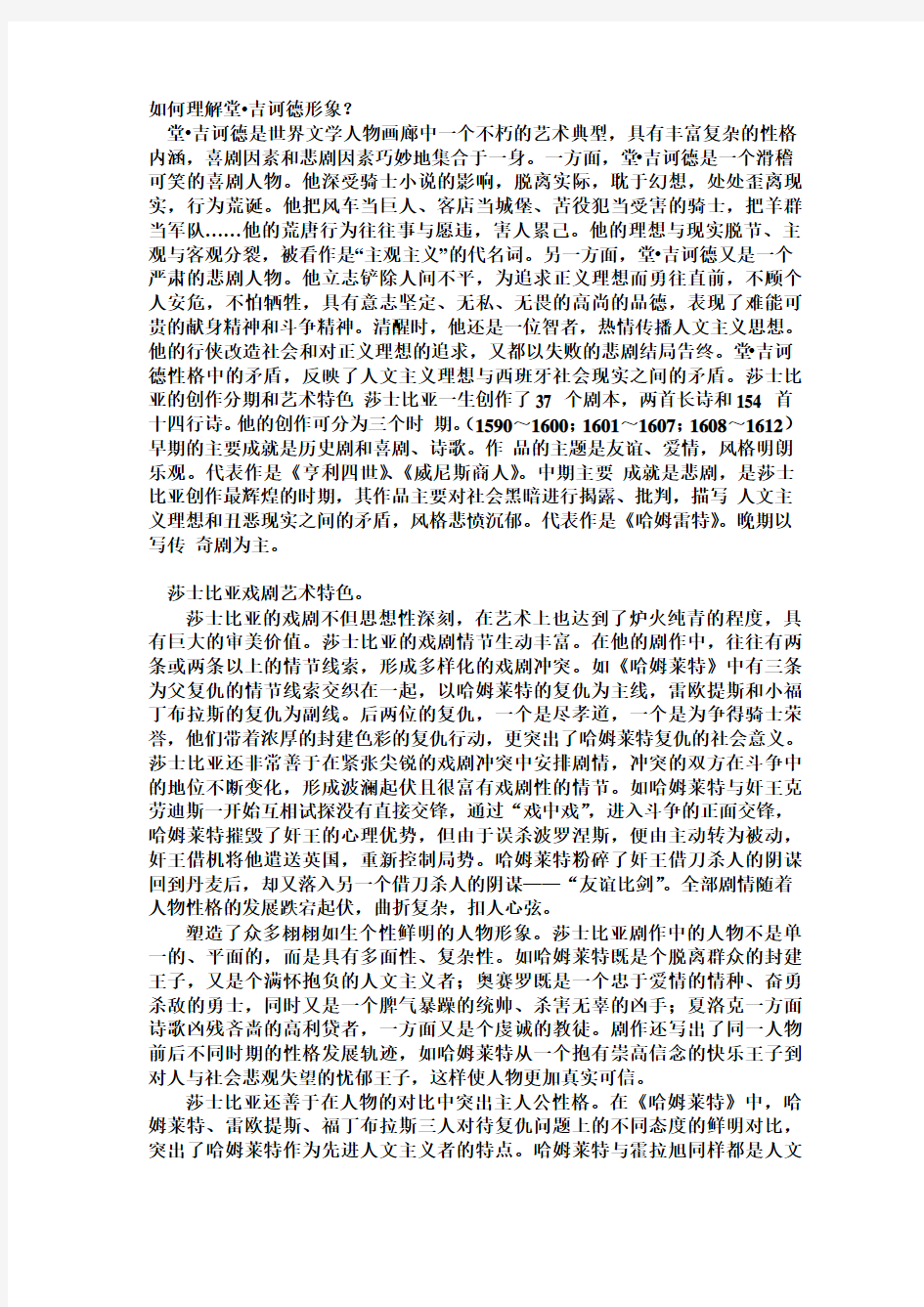

如何理解堂?吉诃德形象?
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具有丰富复杂的性格内涵,喜剧因素和悲剧因素巧妙地集合于一身。一方面,堂?吉诃德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喜剧人物。他深受骑士小说的影响,脱离实际,耽于幻想,处处歪离现实,行为荒诞。他把风车当巨人、客店当城堡、苦役犯当受害的骑士,把羊群当军队……他的荒唐行为往往事与愿违,害人累己。他的理想与现实脱节、主观与客观分裂,被看作是“主观主义”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堂?吉诃德又是一个严肃的悲剧人物。他立志铲除人间不平,为追求正义理想而勇往直前,不顾个人安危,不怕牺牲,具有意志坚定、无私、无畏的高尚的品德,表现了难能可贵的献身精神和斗争精神。清醒时,他还是一位智者,热情传播人文主义思想。他的行侠改造社会和对正义理想的追求,又都以失败的悲剧结局告终。堂?吉诃德性格中的矛盾,反映了人文主义理想与西班牙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莎士比亚的创作分期和艺术特色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了37 个剧本,两首长诗和154 首十四行诗。他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590~1600;1601~1607;1608~1612)早期的主要成就是历史剧和喜剧、诗歌。作品的主题是友谊、爱情,风格明朗乐观。代表作是《亨利四世》、《威尼斯商人》。中期主要成就是悲剧,是莎士比亚创作最辉煌的时期,其作品主要对社会黑暗进行揭露、批判,描写人文主义理想和丑恶现实之间的矛盾,风格悲愤沉郁。代表作是《哈姆雷特》。晚期以写传奇剧为主。
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特色。
莎士比亚的戏剧不但思想性深刻,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具有巨大的审美价值。莎士比亚的戏剧情节生动丰富。在他的剧作中,往往有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情节线索,形成多样化的戏剧冲突。如《哈姆莱特》中有三条为父复仇的情节线索交织在一起,以哈姆莱特的复仇为主线,雷欧提斯和小福丁布拉斯的复仇为副线。后两位的复仇,一个是尽孝道,一个是为争得骑士荣誉,他们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的复仇行动,更突出了哈姆莱特复仇的社会意义。莎士比亚还非常善于在紧张尖锐的戏剧冲突中安排剧情,冲突的双方在斗争中的地位不断变化,形成波澜起伏且很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如哈姆莱特与奸王克劳迪斯一开始互相试探没有直接交锋,通过“戏中戏”,进入斗争的正面交锋,哈姆莱特摧毁了奸王的心理优势,但由于误杀波罗涅斯,便由主动转为被动,奸王借机将他遣送英国,重新控制局势。哈姆莱特粉碎了奸王借刀杀人的阴谋回到丹麦后,却又落入另一个借刀杀人的阴谋——“友谊比剑”。全部剧情随着人物性格的发展跌宕起伏,曲折复杂,扣人心弦。
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不是单一的、平面的,而是具有多面性、复杂性。如哈姆莱特既是个脱离群众的封建王子,又是个满怀抱负的人文主义者;奥赛罗既是一个忠于爱情的情种、奋勇杀敌的勇士,同时又是一个脾气暴躁的统帅、杀害无辜的凶手;夏洛克一方面诗歌凶残吝啬的高利贷者,一方面又是个虔诚的教徒。剧作还写出了同一人物前后不同时期的性格发展轨迹,如哈姆莱特从一个抱有崇高信念的快乐王子到对人与社会悲观失望的忧郁王子,这样使人物更加真实可信。
莎士比亚还善于在人物的对比中突出主人公性格。在《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雷欧提斯、福丁布拉斯三人对待复仇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的鲜明对比,突出了哈姆莱特作为先进人文主义者的特点。哈姆莱特与霍拉旭同样都是人文
主义者,但是遭遇不同、地位不同,霍拉旭理智冷静,哈姆莱特热情深沉,更加反衬出哈姆莱特精神世界的深刻性。莎士比亚也擅长用内心独白手法直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的重要独白有六处之多,每次都推动剧情发展,为完成人物性格塑造起了关键作用。最著名的是第三幕第一场的那段:“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表现了他对人生的思索、苦闷与彷徨。
莎士比亚的戏剧语言丰富多彩,具有个性化、形象化的特点。莎翁是语言大师,他的词汇特别丰富,据统计他剧中用到的词汇量达29000个,远远超过了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他的人物语言,不仅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而且贴和人物当时所处的特定环境,和人物的戏剧动作相衬相依。如哈姆莱特清醒时是典雅的语言,符合王子的身份,在装疯时用的是逻辑混乱、晦涩难解的语言,符合疯子的特点。他还善于使用恰当的比喻、双关语、成语和谐语,不仅丰富了表现力,而且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哈姆莱特形象及其典型意义。
哈姆莱特是一个理想的人文主义者的典型。他的性格是鲜明的、丰富的,也是发展的。
哈姆莱特是丹麦一个年轻的王子、乐观的青年,生活是闲逸的、舒适的,为追求知识,他来到了人文主义的中心——德国的威登堡大学读书,在那儿受到了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对人生和世界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在他的心目中,父王是一个“堂堂的男子”、“理想的君王”、“人”的典范;他的情人奥菲利娅是纯洁、美丽的。整个世界都充满了一片光明。这时他还完全生活在脱离现实的幻想之中,是一个快乐的王子。然而,当他从德国回到丹麦后,母后匆匆改嫁,叔父克劳迪斯娶了母后,篡夺了王位。这一下便使他从美丽的幻想的云端跌入了无底的痛苦的深渊。他悲伤、苦闷,对人生和世界感到失望和厌倦,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接着先王的鬼魂向他揭露了克劳迪斯的阴谋,这像晴天霹雳一样使他震惊。他精神上经受不了这一沉重打击,失去了自持力,于是便趁势装疯,但理智还是清醒的。他看到周围的世界原来是充满了恶德败行的罪恶的世界。他在忧郁中开始了深沉的思考,在装疯中以荒诞的行为使克劳迪斯惶惶不安。就在他观察、思考周围世界的时候,一连串罪恶的事实又发生在他身边:他的同学、朋友一个个卖身投靠奸王,充当克劳迪斯的密探;奥菲利娅也被奸王利用作工具……现实世界处处是邪恶和背叛,他认识到自己的任务不仅仅是报父仇,而是要担当起重整乾坤的重任!他苦苦思索,探求扭转乾坤、恢复正义的途径和手段,又“把后果考虑得过分周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犹豫彷徨、烦闷不安、自谴自责,精神上痛苦到了极点,甚至想到“活下去还是不活”的问题。
忧郁,是哈姆莱特理想破灭后精神状态的一个显著特征。他回国后一系列意外事故的出现,打破了他的幻想,人文主义者视若珍宝的生活理想化为泡影,使他变得忧郁、苦闷:“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但忧郁不是哈姆莱特的天性,而是理想与现实矛盾,理想破灭产生的一种精神状态。
哈姆莱特的另一性格特点是延宕。他把报父仇同拯救国家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不但要报父仇,而且要消灭一切罪恶,按照人文主义的理想来改造现实。然而在强大的邪恶势力面前,尽管他不断探索寻找途径,却始终在决心行动而不知如何行动的
矛盾之中,这就形成了他行动的犹豫延宕。
形成哈姆莱特悲剧的原因,从客观上看是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哈姆莱特是封建社会内部出现的少数先进人物的代表,他与克劳迪斯的斗争,反映了先进人物同社会恶势力抗争,必然导致悲剧结局。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他同情人民的苦难,人民对他有好感;但他即不相信暴力,又不相信群众,孤军奋战,而且不能摆脱宿命论等旧思想的残余。所以,哈姆莱特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人文主义者的悲剧。
莎士比亚通过哈姆莱特的形象概括了新旧交替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思想面貌,写出了人文主义者同黑暗现实的矛盾和斗争,写出了他们探求真理的历程,也写出了他们的悲剧命运。哈姆莱特形象的巨大力量不在于解决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而在于提出现实世界是丑恶的、不合理的,必须进行改革这一根本问题。这也是哈姆莱特所以能成为欧洲文学史上不朽的艺术典型的重要原因。
《伪君子》主题和艺术特点。
《伪君子》通过对心如蛇蝎的答尔丢夫伪装虔诚的揭露与鞭挞,矛头直指教会,突出地批判了宗教伪善的欺骗性与危害性,引起了人民群众对宗教教义和宗教上层人物的怀疑,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分教会的民主倾向。对宗教伪善的欺骗性与危害性的揭露与鞭挞,就是《伪君子》的主题。
《伪君子》在艺术上渗透了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原则,情节单纯集中,自始至终都是为了表现答尔丢夫的虚伪与欺骗;时间在24小时之内,地点在奥尔贡家的客厅,情节全安排在同一地点而不显勉强,艺术上构思精巧。再者,全剧结构严整紧凑,喜剧冲突集中,中心人物与其他人物的基本特征性格鲜明。答尔丢夫虽然到第三幕才出场,但通过前两场开场人物的议论,收到了烘云托月的效果,他的作为、欺骗、影响和权威笼罩了一、二幕,被摆在两派争论的焦点上,这样就收到了单刀直入、一举数得之效,为剧情的发展作了有力的铺垫。第三,喜剧还有机地综合了多种戏剧因素。如打耳光,隔墙偷听、桌下藏人,这是民间闹剧的因素;波奈尔夫人与子孙们的吵闹,奥尔贡的专横,大密斯的反抗和被撵出家门,这是风俗喜剧的因素;奥尔贡几乎家破人亡,这又是悲剧因素。这种独具风格的喜剧手法,使作品既有滑稽戏谑的情趣,又有扣人心弦的紧张气氛。第四,剧中人物的语言高度个性化。答尔丢夫的语言矫揉造作,堆砌词藻,长篇大论地玩弄教义,符合他伪善的性格。道丽娜语言犀利、明快、生动、朴素,显示出她爽朗的性格和来自民间的智慧。
浮士德形象分析。
《浮士德》的主人公浮士德是一种积极进取精神的代表,是一个自强不息、执着探索者的形象。为了人生的真义,为了体察那短暂的、至善至美的一瞬,他不怕以鲜血和灵魂做低押;他在探求人生意义、探索理想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生无所息、坚韧顽强、非凡毅力和品格。他经受了各种诱惑和考验;同梅非斯特打赌,激起他重新探索的信念;热恋的悲剧使他不再追求感官的享受;从政的悲剧使他逃离避现实;古典理想的幻灭,使他重新回到现实中寻找实现理想的途径。他永不满足,永不示弱,探求不止,“无论是在人间或在天上,没一样可满足他的心肠”,始终向上向善。这些便构成性格上最鲜明的特征。这正是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一些渴望摆脱蒙昧、获取真知而勇往直前的知识分子的写照。浮士德又是普通人类的代表,具有人身上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