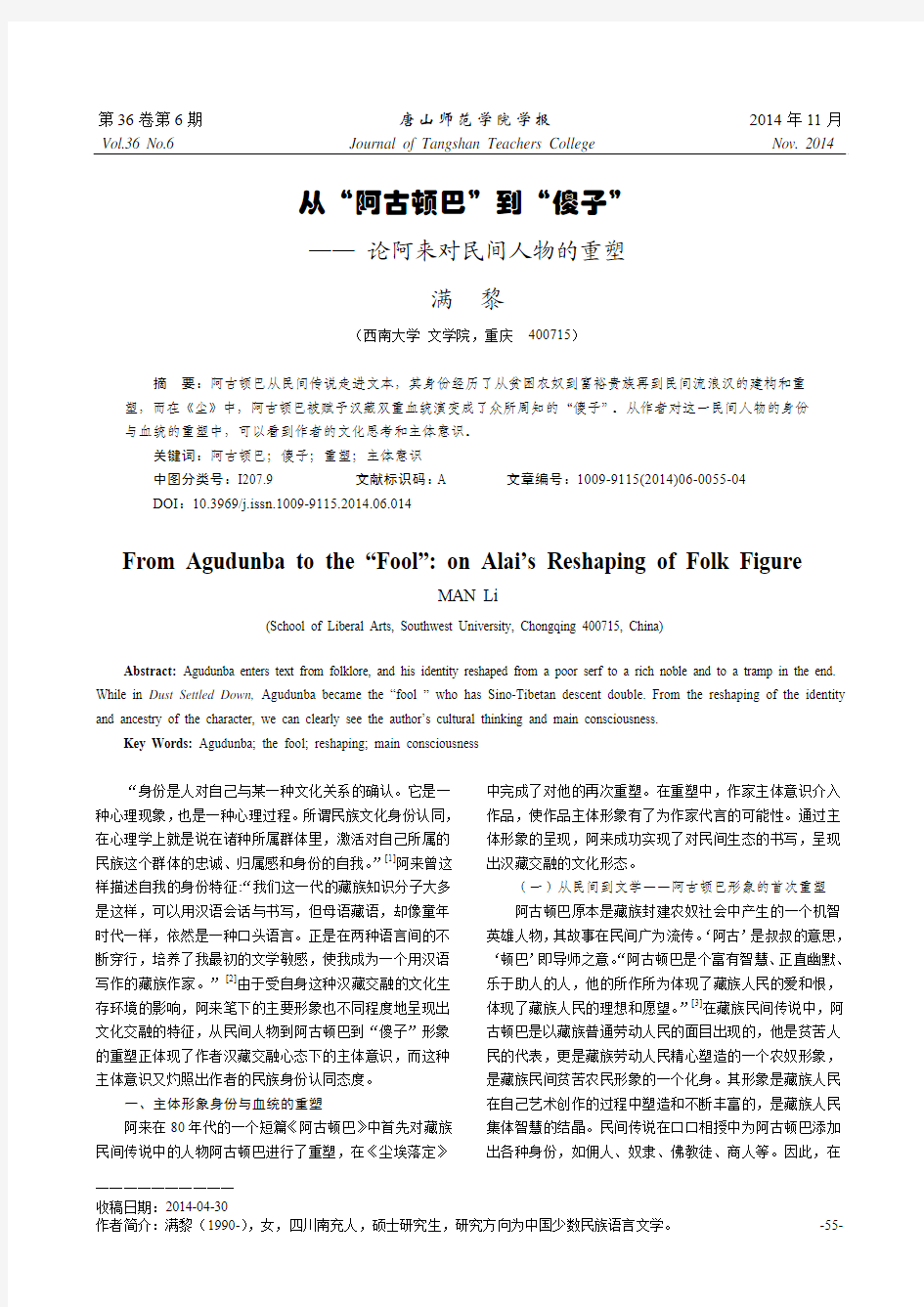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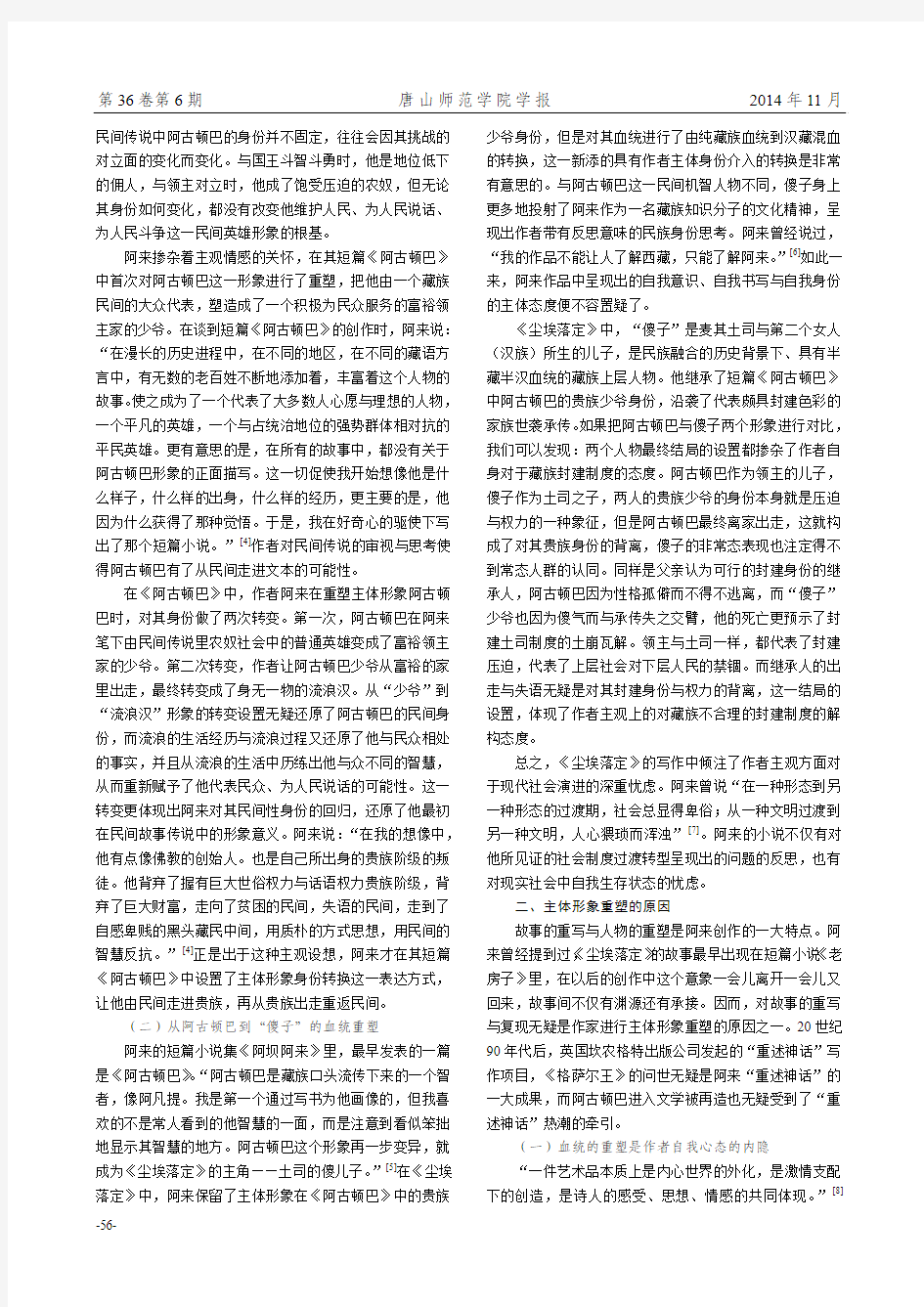
第36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4年11月 Vol.36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14
────────── 收稿日期:2014-04-30 作者简介:满黎(1990-),女,四川南充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55-
从“阿古顿巴”到“傻子”
—— 论阿来对民间人物的重塑
满 黎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阿古顿巴从民间传说走进文本,其身份经历了从贫困农奴到富裕贵族再到民间流浪汉的建构和重塑,而在《尘》中,阿古顿巴被赋予汉藏双重血统演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傻子”。从作者对这一民间人物的身份与血统的重塑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文化思考和主体意识。
关键词:阿古顿巴;傻子;重塑;主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4)06-0055-04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4.06.014
From Agudunba to the “Fool”: on Alai’s Reshaping of Folk Figure
MAN L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Agudunba enters text from folklore, and his identity reshaped from a poor serf to a rich noble and to a tramp in the end. While in Dust Settled Down, Agudunba became the “fool ” who has Sino-Tibetan descent double. From the reshaping of the identity and ancestry of the character, we can clearly see the author’s cultural thinking and main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Agudunba; the fool; reshaping; main consciousness
“身份是人对自己与某一种文化关系的确认。它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过程。所谓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在心理学上就是说在诸种所属群体里,激活对自己所属的民族这个群体的忠诚、归属感和身份的自我。”[1]阿来曾这样描述自我的身份特征:“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2]由于受自身这种汉藏交融的文化生存环境的影响,阿来笔下的主要形象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文化交融的特征,从民间人物到阿古顿巴到“傻子”形象的重塑正体现了作者汉藏交融心态下的主体意识,而这种主体意识又灼照出作者的民族身份认同态度。
一、主体形象身份与血统的重塑
阿来在80年代的一个短篇《阿古顿巴》中首先对藏族民间传说中的人物阿古顿巴进行了重塑,在《尘埃落定》
中完成了对他的再次重塑。在重塑中,作家主体意识介入作品,使作品主体形象有了为作家代言的可能性。通过主体形象的呈现,阿来成功实现了对民间生态的书写,呈现出汉藏交融的文化形态。
(一)从民间到文学——阿古顿巴形象的首次重塑 阿古顿巴原本是藏族封建农奴社会中产生的一个机智英雄人物,其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阿古’是叔叔的意思,‘顿巴’即导师之意。“阿古顿巴是个富有智慧、正直幽默、乐于助人的人,他的所作所为体现了藏族人民的爱和恨,体现了藏族人民的理想和愿望。”[3]在藏族民间传说中,阿古顿巴是以藏族普通劳动人民的面目出现的,他是贫苦人民的代表,更是藏族劳动人民精心塑造的一个农奴形象,是藏族民间贫苦农民形象的一个化身。其形象是藏族人民在自己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塑造和不断丰富的,是藏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民间传说在口口相授中为阿古顿巴添加出各种身份,如佣人、奴隶、佛教徒、商人等。因此,在
第36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4年11月
-56-
民间传说中阿古顿巴的身份并不固定,往往会因其挑战的对立面的变化而变化。与国王斗智斗勇时,他是地位低下的佣人,与领主对立时,他成了饱受压迫的农奴,但无论其身份如何变化,都没有改变他维护人民、为人民说话、为人民斗争这一民间英雄形象的根基。
阿来掺杂着主观情感的关怀,在其短篇《阿古顿巴》中首次对阿古顿巴这一形象进行了重塑,把他由一个藏族民间的大众代表,塑造成了一个积极为民众服务的富裕领主家的少爷。在谈到短篇《阿古顿巴》的创作时,阿来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藏语方言中,有无数的老百姓不断地添加着,丰富着这个人物的故事。使之成为了一个代表了大多数人心愿与理想的人物,一个平凡的英雄,一个与占统治地位的强势群体相对抗的平民英雄。更有意思的是,在所有的故事中,都没有关于阿古顿巴形象的正面描写。这一切促使我开始想像他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出身,什么样的经历,更主要的是,他因为什么获得了那种觉悟。于是,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写出了那个短篇小说。”[4]作者对民间传说的审视与思考使得阿古顿巴有了从民间走进文本的可能性。
在《阿古顿巴》中,作者阿来在重塑主体形象阿古顿巴时,对其身份做了两次转变。第一次,阿古顿巴在阿来笔下由民间传说里农奴社会中的普通英雄变成了富裕领主家的少爷。第二次转变,作者让阿古顿巴少爷从富裕的家里出走,最终转变成了身无一物的流浪汉。从“少爷”到“流浪汉”形象的转变设置无疑还原了阿古顿巴的民间身份,而流浪的生活经历与流浪过程又还原了他与民众相处的事实,并且从流浪的生活中历练出他与众不同的智慧,从而重新赋予了他代表民众、为人民说话的可能性。这一转变更体现出阿来对其民间性身份的回归,还原了他最初在民间故事传说中的形象意义。阿来说:“在我的想像中,他有点像佛教的创始人。也是自己所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叛徒。他背弃了握有巨大世俗权力与话语权力贵族阶级,背弃了巨大财富,走向了贫困的民间,失语的民间,走到了自感卑贱的黑头藏民中间,用质朴的方式思想,用民间的智慧反抗。”[4]正是出于这种主观设想,阿来才在其短篇《阿古顿巴》中设置了主体形象身份转换这一表达方式,让他由民间走进贵族,再从贵族出走重返民间。
(二)从阿古顿巴到“傻子”的血统重塑
阿来的短篇小说集《阿坝阿来》里,最早发表的一篇是《阿古顿巴》。“阿古顿巴是藏族口头流传下来的一个智者,像阿凡提。我是第一个通过写书为他画像的,但我喜欢的不是常人看到的他智慧的一面,而是注意到看似笨拙地显示其智慧的地方。阿古顿巴这个形象再一步变异,就成为《尘埃落定》的主角——土司的傻儿子。”[5]在《尘埃落定》中,阿来保留了主体形象在《阿古顿巴》中的贵族少爷身份,但是对其血统进行了由纯藏族血统到汉藏混血的转换,这一新添的具有作者主体身份介入的转换是非常有意思的。与阿古顿巴这一民间机智人物不同,傻子身上更多地投射了阿来作为一名藏族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呈现出作者带有反思意味的民族身份思考。阿来曾经说过,“我的作品不能让人了解西藏,只能了解阿来。”[6]如此一来,阿来作品中呈现出的自我意识、自我书写与自我身份的主体态度便不容置疑了。
《尘埃落定》中,“傻子”是麦其土司与第二个女人(汉族)所生的儿子,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半藏半汉血统的藏族上层人物。他继承了短篇《阿古顿巴》中阿古顿巴的贵族少爷身份,沿袭了代表颇具封建色彩的家族世袭承传。如果把阿古顿巴与傻子两个形象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人物最终结局的设置都掺杂了作者自身对于藏族封建制度的态度。阿古顿巴作为领主的儿子,傻子作为土司之子,两人的贵族少爷的身份本身就是压迫与权力的一种象征,但是阿古顿巴最终离家出走,这就构成了对其贵族身份的背离,傻子的非常态表现也注定得不到常态人群的认同。同样是父亲认为可行的封建身份的继承人,阿古顿巴因为性格孤僻而不得不逃离,而“傻子”少爷也因为傻气而与承传失之交臂,他的死亡更预示了封建土司制度的土崩瓦解。领主与土司一样,都代表了封建压迫,代表了上层社会对下层人民的禁锢。而继承人的出走与失语无疑是对其封建身份与权力的背离,这一结局的设置,体现了作者主观上的对藏族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解构态度。
总之,《尘埃落定》的写作中倾注了作者主观方面对于现代社会演进的深重忧虑。阿来曾说“在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过渡期,社会总显得卑俗;从一种文明过渡到另一种文明,人心猥琐而浑浊”[7]。阿来的小说不仅有对他所见证的社会制度过渡转型呈现出的问题的反思,也有对现实社会中自我生存状态的忧虑。
二、主体形象重塑的原因
故事的重写与人物的重塑是阿来创作的一大特点。阿来曾经提到过,《尘埃落定》的故事最早出现在短篇小说《老房子》里,在以后的创作中这个意象一会儿离开一会儿又回来,故事间不仅有渊源还有承接。因而,对故事的重写与复现无疑是作家进行主体形象重塑的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后,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的“重述神话”写作项目,《格萨尔王》的问世无疑是阿来“重述神话”的一大成果,而阿古顿巴进入文学被再造也无疑受到了“重述神话”热潮的牵引。
(一)血统的重塑是作者自我心态的内隐
“一件艺术品本质上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创造,是诗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体现。”[8]
满 黎:从“阿古顿巴”到“傻子”
-57-
同是文学作品的诗与小说都隐含着作者主观态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设置往往倾注了作者的自身情感,掺杂着作家自己对特定问题的思考,渗入了作者的主观意识。
母亲是汉族人,父亲是藏族人,面临双重可以选取的文化身份,阿来有自己文化身份的疑惑,并且受到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双重压力。作家阿来出生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因为在地理上不在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带,不懂藏文,不能接触藏语的书面文学”[2],这种略微尴尬的文化处境,让他具有鲜明意识的藏族书写保持着小心翼翼的心态。文学界对少数民族作家身份的质疑,无疑也让阿来这个具汉藏双重血统却不懂藏文的作家,在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书写时满心忧虑。阿来说“生活习惯最终决定了我自己在血缘上的认同感。”阿来在一个被汉化的少数民族地区长大,说汉话、穿汉服、接受汉文化教育、接触的是同被汉化的人,这种现实处境无疑造成了作者在自身民族文化面前的失语心态。毫无疑问,当作者有意识地重返自身民族文化时,这种略为尴尬的处境让阿来陷入“被怀疑”的忧虑中。
拥有正宗藏族血统的民间智者阿古顿巴在《尘埃落定》中被作者重塑为具有汉藏双重血统的“傻子”,这实际上包含了作者自己对汉藏文化交融的看法。作为以书写藏族文化而出名的少数民族作家阿来并不将自己简单定位为少数民族作家,他说:“我写藏族文化,不是只关注了藏族文化,文学应该关注全人类全宇宙的情感、命运,文学表达的不是差异性而是普遍性”[9]。
“傻子”双重血统的建构无疑是对自身汉藏文化差异的再现,是作者呈现两种文化交融形态的一个表现形式,也是作者自我心态的一个投影。
(二)主体形象的重塑是作者文化心态的外化 在一次接受记者的访谈中,阿来说道:“藏文化……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同时它还有一个大家共同遵从的基本的伦理、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自然观,有统一的关于世界的看法,这是汉人缺失的,但它问题是僵化与保守;而汉文化开放、积极。”[10]阿来熟知汉、藏文化各自的优劣,在两种文化语境中,阿来的写作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的表达空间。文学是人学,作品主体形象的话语不仅代表了自身的文本角色,也灼照着作者主体的情感和意识。傻子形象双重血统的设置,渗透着作者主体的汉藏文化心态和身份反思,是自身文化心态的外化。
“傻子”的死亡代表了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末代土司制度的土崩瓦解,试想:如果“傻子”得以保全,土司制度以其具有双重血统的身份延续,在传承的过程中,完全无法避免汉化的可能。汉化无疑是对藏族文化生存形态的一种重置,但是在作者看来,汉化作为目前少数民族生存的趋势,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消解。一方面,作者对汉藏文化交融共处的文化生存状态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又
对这种共融而产生的汉化影响忧心忡忡。自西藏解放以来,汉族文化入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汉族文化入侵导致藏文明汉化与凋零的现实境况。在少数民族文明面前,汉文化以其庞大受众展现出了强势的影响力,可以说,傻子的最终“死亡”是对汉文化强势入侵的一种解构。土司制度最终走向消亡而不是以重置的方式保存下来,一方面有作者对汉化的忧心,另一方面也有对不合理土司制度走向消亡的态度确认。阿来说“不要仅仅因为喜欢自己的民族就只关注自己的民族,表现民族应该只是自己的一个入口”[9]。在《尘埃落定》中,阿来清醒地表露了对于汉藏两种文化交融的主观态度,站在汉藏交融的文化立场上,撇清了人们认定的少数民族专属写作的狭义立场。
三、主体形象重塑的文学意义
阿来以对民间的关注和对民间资源的利用表达着作品的人民性诉求。文学的人民性涉及着文学的民族性,阿来有倾向性的对藏民族民间资源的开掘,潜在地表现出了他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态度,因而,他的作品不仅是民间的文学还是人民的文学。
(一)民间资源再造的意义
民间资源在当今文学创作中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有待发掘,阿来无疑正是这样一位掘井人。阿来创作中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开掘,丰富着现代文学的多样性,也填补着文学史上民间文学并不发达的空缺。
“傻子”形象由民间人物演化而来,这种重塑型的文学形象为后世文学创造提供了借鉴经验。在傻子形象重塑时,作者保留了原型身上的某些民间特质,同时也赋予了他新的时代内容,使新与旧、传统与流行的文化元素呈现出共生共融的状态,让他身上看似笨拙的民间智慧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成为新时代仍不褪色的丰碑性民间英雄形象。阿古顿巴这一原型的选取其实包含了作者的民间看法、民间态度和老百姓的立场,是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看法、态度和立场相对应的。阿来说:“过去,我们在写作中主要是把民间文学当作一种题材资源,并不认为它会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给人什么指导。我觉得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浪费了巨大的民间宝藏。”[11]阿来发现了民间资源更深广的价值,他对民间资源的开掘利用,不仅更大意义上地拓展了藏民族民间资源的文化价值,还赋予了其更广的指涉意义和内涵,使得民间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地位越来越引人注目。
(二)民间写作的“人民性”诉求
“‘人民性’就是从广大人民立场出发,表现他们的利益、愿望和情感。从作品的角度上讲,人民性就是要表现人民的心理、人民的希望与期待,也就是反映劳动群众的利益。从作家的角度讲,人民性就是创作主体要表现人民大众的情感、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12]对人民性的
第36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4年11月
-58-
关注是一个作家民间情感的呈现,从早期《格萨尔王传》对民间史诗的重写,到一系列短篇对于民间人物的关照,再如《尘埃落定》《空山》等重要作品,对民间故事、民间习俗的穿插运用,阿来建构起了一个自己的藏族民间世界,这个世界给了读者更多的了解藏族文明的可能性。无论从作品还是作家角度来讲,阿来的民间写作都指涉着普通大众的心理和期待。格萨尔王代表了藏族人民的希望、荣誉与自信,阿来以《格萨尔王》重述了藏民族口传文化中的英雄人物,使藏族人民心理上得到莫大满足。阿古顿巴代表了人们惩奸除恶的愿望,寄托着人们反抗压迫的期待,阿古顿巴走进文学更是劳动群众的利益得以彰显的表现。阿来的作品有对英雄人物的光荣史实的重述,也有对普通藏族民众生存状态的呈现,更有对普通大众生活的诉求的表达,这些人民性诉求奠定了他在民间文学中的地位。
四、结语
阿来讲述民间故事,使用民间话语,作品中倾注着民间热情,这便使他的作品有了扩散到民间的可能性;而阿古顿巴这一民间形象使文学走出殿堂,走进民间,又使主体形象有了与民众亲近的可能性。关照主体形象的民间特质这一主体创作倾向,不仅使阿来笔下的主体形象在民间文学中取得了独树一帜的话语权,也使阿来的民间书写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夺取了自己的一片阵地,更成就了阿来自己在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可以说阿古顿巴从民间走进文本是作者对民间资源的关注,而对其身份与血统的重塑则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自身主观心理意识的左右,是作者主观文化心态的外化,是对具有双重血统的写作主体立场的忧虑,也夹杂着自身对社会过渡和文明形态过渡的思索。
[参考文献]
[1] 杨霞.尘埃落定的空间文化书写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2010:51.
[2] 阿来.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J].美文,2007(7):54-55. [3] 莫福山.藏族文学[M].成都:巴蜀书社,2003:53.
[4] 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J].民族文学研究,2001(3):
90-93.
[5] 沈沣.阿来出版短篇小说集《阿坝阿来》[EB/OL].中国
作家网:https://www.doczj.com/doc/408746770.html, 2004-03-18. [6] 汪兆骞.一个西藏人的文学流浪——记作家阿来[N].人
民日报海外版, 2004-08-20.
[7] 阿来.《尘埃落定》后记[A].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8] 艾布拉姆斯.张照进,童庆生译.镜与灯——浪漫主义文
论及批评传统[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20. [9] 明江.阿来:民族文学表达的不是差异性[EB/OL].http://
https://www.doczj.com/doc/408746770.html,,2009-4-9.
[10] 易文翔,阿来.写作:忠实于内心的表达——阿来访谈录
[J].小说评论.2004(5):17-22.
[11] 阿来.文学创作中的民间文化元素[N].解放日报理论
版,2007-02-25(8).
[12] 刘建强.人民性——文学永久的希望[J].吉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2(3):63-66.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阿来《尘埃落定》中‘傻子’形象解读 摘要: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尘埃落定》从独特的视角叙说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讲述了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故事。然而作者为什么要让一个“傻子”居于作品中心,“傻子”对于整个作品、对于作者、对于读者,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笔者以为,在作品中,主人公并不傻,“傻”是他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护身的“铠甲”和进攻的“利器”;对作者来说,“傻”是作者陈述嘉绒地区土司时代的真实历史的需要;而对于读者来说,“傻”与“智”的反差,则进一步促进了与作品的融合,有利于读者形成审美高峰体验。 关键词:阿来《尘埃落定》傻子价值生存审美体验 恩格斯曾这样评价巴尔扎克的小说集《人间喜剧》:“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阅读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尘埃落定》,让我对恩格斯以及巴尔扎克的这两段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是这部作品引领我们抚摸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与历史相比,它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更具吸引力。正如电视剧《三国演义》片尾曲所唱的那样“历史的星空闪烁几多星……”。在作家阿来为我们叙述的这段历史中,一个个挥之不去的形象总在脑海里浮现:老谋深算而残忍霸道的麦其,凶残斗狠、有勇无谋的麦其的草包大儿子,因出身低贱而特别注重身份的麦其土司二太太,汪波土司的忠勇而愚昧的奴才,放荡但却头脑简单的央宗,暴戾而忠诚的索郎泽郎,腼腆但灵巧的尔依,忠诚而又善良的卓玛,淫荡而又贪慕权势的塔娜…… 然而在《尘埃落定》这部作品所建构的历史舞台上,始终处于舞台中心位置的却是一个“傻子”——麦其土司家的二公子,一个麦其酒醉后播种结出的畸形果实。那么,作家阿来为什么要让二少爷成为一个“傻子”?又为什么要让他站在舞台中央,其间有什么深意?它对于读者的
阿来短篇小说读后感 落在尘世 《老房子》是阿来1986年12月11日(这个时间虽多次考证仍无法确认)完成于马尔康的短篇小说。它顺着人物失而复得的意识流,流荡出一个男子卑微的人生,以及一条隐蔽的传统--不是表面上的少数民族风俗,而是东方精神生活的传统。《老房子》为我呈现出的,是一种不无宗教精神的世俗生活的传奇,也通过某种不无可能性的爱,映射出现实人生的凉薄与无为。 土司的门房一百零八岁时,死而复生,又被大地唤醒。在人们的话语中,他便是那个因情而死的门房,人们不知道他死而复生。在传说中,土司的门房害了相思病。他的死是为了土司太太,他的活是为了读者。作者让他活过来,为我们讲述自己的人生。 永远被女人纠缠的男人。他永远为他人而活。他的世界里没有亲人,只有女主人,那个在他眼里身份十分高贵的美丽女人。土司太太被遗弃,被外来的兵强奸,太太对他说:“有了的娃娃是你的娃娃。”门房内心感到光荣。 他忠诚地守着太太,看着她在别的男人怀抱里打滚。
太太生第二个野孩子的时候死了,他也死了。但是最后仍然由他来给我们讲这个故事。 “他曾在八十六岁上梦见自己和太太交合。” 第二次难产太太至死也没说:“是你的娃娃。”他于是对自己追问起来并且自己回答:“是我的娃娃。” 这个故事有些无法破解的神秘感。一旦有所发现则令人十分自得。 语言像天上的白云一样优美诗意,又富于乌云般的暗示和象征。 “地板上满是过去日子的灰烬。” “老房子仍像一个骨质疏松的梦境一样静静耸立。” “那具军官的骷髅向他切齿微笑。” 土司的门房所感知的爱情是实实在在的,从他对于声音与色彩的敏锐感觉中。作者用自己的想象为读者进行了转述。我相信那些暗示感情的文字里,有门房曾经年轻有力的心脏的跳动,更有作者训练有素、不由自主的推敲。 太太被军官强奸时,门房注意地听着,“居然传来女人纵情的呻吟”。这是个复杂叙事的结果。作者是在退出道德的框框之后,还原人物不无嫉妒的感情真相,还是在情节进行中适度合理地夸张呢?这真的很难说。但是这种入木
关于“阿来小说《尘埃落定》研究”的论文(定稿)
阿来《尘埃落定》中‘傻子’形象解读 摘要: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尘埃落定》从独特的视角叙说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讲述了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故事。然而作者为什么要让一个“傻子”居于作品中心,“傻子”对于整个作品、对于作者、对于读者,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笔者以为,在作品中,主人公并不傻,“傻”是他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护身的“铠甲”和进攻的“利器”;对作者来说,“傻”是作者陈述嘉绒地区土司时代的真实历史的需要;而对于读者来说,“傻”与“智”的反差,则进一步促进了与作品的融合,有利于读者形成审美高峰体验。 关键词:阿来《尘埃落定》傻子价值生存审美体验 恩格斯曾这样评价巴尔扎克的小说集《人间喜剧》:“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阅读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尘埃落定》,让我对恩格斯以及巴尔扎克的这两段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是这部作品引领我们抚摸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与历史相比,它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更具吸引力。正如电视剧《三国演义》片尾曲所唱的那样“历史的星空闪烁几多星……”。在作家阿来为我们叙述的这段历史中,一个个挥之不去的形象总在脑海里浮现:老谋深算而残忍霸道的麦其,凶残斗狠、有勇无谋的麦其的草包大儿子,因出身低贱而特别注重身份的麦其土司二太太,汪波土司的忠勇而愚昧的奴才,放荡但却头脑简单的央宗,暴戾而忠诚的索郎泽郎,腼腆但灵巧的尔依,忠诚而又善良的卓玛,淫荡而又贪慕权势的塔娜…… 然而在《尘埃落定》这部作品所建构的历史舞台上,始终处于舞台中心位置的却是一个“傻子”——麦其土司家的二公子,一个麦其酒醉
阿来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身份认同 【摘要】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是阿来等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中的鲜明特色。毫无疑问,这是民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生命意识的觉醒。阿来的小说创作既坚持不懈地把艺术触角深入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在茫茫的历史迷雾中寻找民族文化的踪迹;又在不断地寻找中为民族文化的当代转换和重构探寻着超越之路。 【关键词】阿来小说文化身份认同超越 阿来,当代著名的藏族作家,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尘埃落定》,1988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引起了评论界对阿来文学创作更多的关注。阿来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其小说创作成果,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最高成就,阿来也成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的评论,往往绕不开对“民族文学”这一范畴的解读和阐释。那么什么事民族文学那?“从广义上来说,作为生命个体的创作,所有的文学,都是民族文学,都是由具有独特文化身份的生命个体创作的。每一个作家,都是以一定的文化身份进行创作的,也必然地要进行他所选择的文化表达,也就是说,任何一部作品,在作家进行创作的时候,就自然的获得了某种文化意义,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换句话说,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是民族文学的创作,任何作品,都是民族文学的作品。”[1]但在中国以汉族为绝对主体、各民族共存的多民族背景下,民族文学又有了特别的意义,一般指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文学,即少数民族文学,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界定,一是作家是少数民族,二是作品具有民族特色或者反映了民族生活。阿来的小说创作具有以上鲜明的特点。他从本民族的深厚文化积淀中汲取养分,通过文学话语,来建构自我作为藏民族个体的文化观。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并没有陷入“民粹主义”偏执的狭隘视角。在对汉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比较中,使作者对自我的民族身份和本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 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是阿来等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中的鲜明特色。毫无疑问,这是民
阿来的如花世界阅读答案(2012茂名中考) 阿来的如花世界 迟子建 ①阿来与花,是否有着前世的姻缘?至少,我没见过像他那么痴迷于花的男子!我与他多次同行参加中外文学交流活动,无论是在新疆、黑龙江,还是在俄罗斯、意大利或是阿根廷,当一行人热热闹问地在风景名胜前留影时,阿来却是独自走向别处,将镜头聚焦在花朵上。花儿在阳光和风中千姿百态,赏花和拍花的阿来,也是千姿百态。这时的花儿成了隐秘的河流,而阿来是自由的鱼儿。印象最深的是他屈膝拍花的姿态,就像是向花儿求爱。 ②未认识阿来之前,读了令他名声大噪的《尘埃落定》,判定写它的人一定是个内心世界极其丰富的人。比起他的小说,阿来不高大,但他气质不俗,面上总是洋溢着平和的微笑,走起路来微微踮脚,富有喜剧色彩,整个人就像一首精短的抒情诗,与他热爱的花朵相得益彰。他幽默,睿智,豪爽,率性,与他同行,就是与快乐同行。记得在阿根廷,一个月色很美的夜晚,在一家乡村旅馆里,阿来请全团的人喝酒,他喝兴奋了,歪戴着帽子,拍手舞蹈着,唱起藏族的《祝酒歌》,那是我那一年听到的最动人的旋4.阿来如果不写小说,一定是个出色的歌手。他的歌声深情而忧郁,把我们深深感染了,大家情不自禁地跟着他唱起家乡的歌谣。那个夜晚的阿根廷的月亮,一定成了扩音器,把来自大地的歌声,播撒到了天庭。
③阿来是个会享受生活的人。他常带上钟爱的相机,带上书和茶,独自驾车出游。他的博客和微博,像花园,也像森林氧吧,你走进那里,总能看到花儿的影子,嗅到植物的清新之气。他的作品,也是这样的充满了生机,大气而唯美,绝无顾影自怜的小伤感,更无貌似深刻的装神弄鬼。他有一支开阔而富有韵致的笔。众生在他笔下,都是平等的。如果说好小说是露珠的话,阿来的文字幻化成的就是露珠,熠熠闪亮,有着经典的光泽。《尘埃落定》之于阿来,是一顶沉重的桂冠。如果是一个心在庙堂的作家,可能会就此迷路,不知所向,失去创造力。而阿来是个被山峦照耀着的作家,是被河流滋养着的作家,这样的作家,本身就是一座山,就是一条河,在他自己的疆域驰骋,永不疲倦,留下艺术的脚步。所以我们能在《尘埃落定》之后,仍然能听见《空山》的回音,能看见闪光的《格萨尔王》。 ④阿来出生于四川省阿坝州的藏区,有藏族血统。记得他在墨西哥,为母亲买了一串珊瑚项链。他提着项链对我说,一串好的珊瑚项链,就是一个藏族女人的梦。阿来写过诗,他的话充满诗意。他对藏族的感情,除了融汇到作品里,还体现在他的言论上。记得他写过一篇关于西藏的文章,没有那种强加于人的说教,他褪去了西藏那层“外人”幻想的神秘色彩,还原了一个历史的西藏,现实的西藏,文化的西藏。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把一个越来越形容词化的西藏,客观地厘清,成为一个名词的西藏。这样的西藏立场,深刻,全面,充满人性。 ⑤阿来喜欢读书,今年我们在意大利参加首届中意文学论坛,在听完阿来的演讲后,同样饱学诗书的清华大学教授格非,高度赞扬他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4小题,16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面小题。 马车夫 阿来 这个人身材瘦小,脸上还布满了天花留下的斑斑印迹,但他却是机村最好的骑手,他骑在马上,就跟长在马背上一样自在稳当。机村人认为,这样的人用马眼看去,会有非常特别的地方。 试驾马车那一天,麻子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他骑着一匹马徘徊在热闹的圈子外边。人们扎成一圈,看村里的男子汉们费尽力气想把青鬃马塞进两根车辕之间,用那些复杂的绊索使它就范。折腾了很长时间,他们也没有能给青鬃马套上那些复杂的绊索。青鬃马又踢又咬。人们这才把眼光转向了勒马站在圈子之外的麻子。 在众人的注视下,他脸上那些麻坑一个个红了。他抬腿下了马背,慢慢走到青鬃马跟前。他说:“吁——”青鬃马竖起的尾巴就慢慢垂下了。他伸出手,轻拍一下青鬃马的脖子,挠了挠马正呼出滚烫气息的鼻翼,牲口就安静下来了。这个家伙,脸上带着沉溺进了某种奇异梦境的浅浅笑容,开始嘀嘀咕咕地对马说话,马就定了身站在两根结实的车辕中间,任随麻子给它套上肩轭和复杂的绊索。中辕驾好了,两匹边辕也驾好了。 人群安静下来。 麻子牵着青鬃马迈开了最初的两步。这两步,只是把套在马身上那些复杂的绊索绷紧了。麻子又领着三匹马迈出了小小的一步。这回,马车的车轮缓缓地转动了一点。但是,当麻子停下了步子,轮子又转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走啊,麻子!”人们着急了。 麻子笑了,细眼里放出锐利的亮光,他连着走了几步。轮子就转了大半圈。轮箍和轮轴互相摩擦,发出了旋转着的轮子必然会发出的声音。 马也像一只鸟,有点胆怯又有点兴奋地要初试啼声,刚叫出半声就停住了。 马也竖起了耳朵,谛听身后那陌生的声音。 他又引领着马迈开了步子。 三匹马,青鬃马居中,两匹黑马分行两边,牵引着马车继续向前。转动的车轮终于发出了完整的声音: 叽——吭! 前半声小心翼翼,后半声理直气壮。 那声音如此令人振奋,三匹马不再要驭手引领,就伸长脖颈,耸起肩胛,奋力前行了。 麻子从车头前闪开,在车侧紧跑几步,腾身而起,安坐在了驭手座上,取过竖在车辕上的鞭子,凌空一抽,马车就蹿出了广场,向着村外的大道飞驰起来。 从此,一直蜗行于机村的时间也像给装上了飞快旋转的车轮,转眼之间就快得像是射出的箭矢一样了。 这不,马车开动那一天的情景好像还在眼前,那些年里,麻子一脸坑洼里得意的红光还在闪烁,马车又要成为淘汰的事物,因为,拖拉机出现了。拖拉机不但比马车多出了四只轮子,更重要的是,一台机器代替了马匹。拖拉机手得意地拍拍机器,对围观的人说:“四十匹马力。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四十匹马。” 人群里发出一声赞叹。 拖拉机手还说:“你们去问问麻子,他能不能把四十匹马一起套在马车前面?” 其实,拖拉机手早就看见麻子勒在手里的缰绳,骑在他心爱的青鬃马上,呆在人圈外面,那情形,颇像是第一次给马车套马时的情形。但他故意要把这话让麻子听见。麻子也不得不承
2020年高考(文学类文本阅读)名家名作精练 ——阿来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狩猎 阿来 军分区的侦察参谋,银巴;农牧局的小车司机,秦克明;我呢,专业给文工团歌手填写歌词。我们是偶然凑在一起的狩猎伙伴,因为大家的身份脾气极不相同,更何况因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几乎我们渴望到手的飞禽走兽都受到法律保护了。 我们沿着小径向深山里进发。四周一片静谧,在树林变得稀疏的地方,出现了黑色圆润的新鲜獐子粪便。再后来,就看到了那个棚寮,那个以前许多猎手相继过夜,相继修缮过的棚寮。 我们坐下来歇气,突然,一只獐子从棚子里飞蹿而出,连银巴也来不及举枪就蹿下山坡了。它站在对面一座孤立的小山冈上向我们瞭望,距离太远了,超过了枪的射程。 天很快就黑了。还有只獐子在周围逡巡不去,一直弄出许多声响。银巴说:“要出来你就出来吧。”不久,那獐子果然就从一团灌木后探出了脑袋,双眼十分明亮。我端起小口径运动步枪,瞄准致命的额头的中央。勾动枪机,一声枪响,獐子纵身跃,黑暗中传来一串树枝摇动的声音。 “是只母獐。”秦克明很有把握地说。 “算了,睡吧。”我躺上了吊床,秦克明裹件大衣半倚在底下藏过獐子的松枝上,银巴钻进了睡袋。 睡着一阵,醒来。天上的星光消失了,下雨了,只听到树叶在雨声中沙沙作响。恍惚中,我还看到了雾气从谷底慢慢升向我们过夜的这个地方。 轰然一声枪响,把我从似梦似醒的状态中彻底震醒了。“麝香!”银巴端起枪大叫,显出一副极不平静的样子:“我都看到它的獠牙了!” “公獐子都有獠牙,它们的肚脐眼就是价比黄金的麝香。”我觉得他大惊小怪。 而经常为一点小事神经过敏的秦克明这时倒过分平静了。 他们两人重新拨燃火,默无声响地喝起酒来了。 我的吊床在轻轻地左右摇晃。他们好像有心事。而我能深入他们的内心吗?我们只是在狩猎时建立起的一种短暂的伙伴关系…… 终于,那些松鸡嘎嘎地叫开了,天就要亮了。雨仍然下着,雨水渐渐被天色照亮,被雨水淋湿的树叶也被渐渐照亮了,那是一种柔和、纯粹、圣洁的光亮,竟然令人产生置身于仙境的感觉。 我们附近的潮湿的泥地里,一夜之间长出了蘑菇!银巴说:“我打个赌,你吃不完这些蘑菇。”说完,他就提枪钻进了树林。果然,周围地上,那些被松针覆盖的土正被一点点拱起,开裂,最多半个来小时,一群蘑菇又破土而出了。 我们背后突然传来羊子似的哀叫声。 一声,两声,焦灼、悲哀、凄凉。那羊子似的叫声渐渐近了。终于一只母獐子从雨水中走了出来,它被雨水完全淋湿了,丰满的乳房里奶水自己渗漏出来。看来,它很久没有给幼獐喂奶了。 棚寮深处的干枯松枝底下传出了一个幼獐的声音,它和我们悄然过了一夜而我们竟然毫无知觉。我们两人同时跃起扑向那堆松枝,底下传来一声惨叫。我们抱出那只哆嗦不已的幼獐,它的一只腿在我们的扑
大智若愚阿来《尘埃落定》读后感藏族作家阿来的作品《尘埃落定》从二少爷傻子的生活环境和情感历程中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生动活泼,表面“大愚”实则“大智”的傻子形象。作品以一个傻子的叙述视角,以独特的文学表现形式和独特的叙事方法展现了藏族土司制度有盛而衰,由存而亡的历史进程。 《尘埃落定》讲述了一个古老家族兴衰的故事,这个家族便是麦其土司,作家把家族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通过家族的兴衰显示了民族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宿命。小说围绕傻子的人生荣辱和生命沉浮来展开故事,他的命运史构成了小说的情节主线。作品在展示傻子的人生遭遇和情感历程中再现了藏族封建土司制度由盛而衰、由存而亡的历史过程,为走向没落的封建土司制度献上了一首深沉的挽歌。 作家选择他作为生活的切入点和故事的叙述者,这保证了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跟随二少爷的脚步,你会看到土司一家饮食起居的奢侈,农奴及其子女生活的艰难困苦;你会看到土司制度下土司就是“法”以及以“法”的名义出现的刑罚的惨无人道;你会看到这里不同于外界的婚姻习俗,甚至连这片土地上厕所的样子都能如亲眼所见。在小说的整个叙述中,所有发生的事件——关于外部世界的真相,土司家族由兴盛到衰亡的历史,人物的命运,
都是由一个“傻子”的视角讲述和表现出来的,而傻子的所有表现又充满了不确定性,象征性,隐喻性,荒诞性和神秘性。 从这个人物所经历的生命过程中,可以发现同样作为人的我们自己的某种影子:他的渴求之中有着人所共有的渴求;他的理想之中有着人所共有的理想,即他的“既傻又不傻”和实际上的不傻,一如现代人的生存景观,两者之间并没有质的差别。其实,体现在傻子二少爷身上的所谓的“傻”,便是他的不识时务,不谙功利或不入世俗,一切顺从天性,其中也包括了他对人性的选择与对人世的好恶,也正因为“傻”,才使他进入了“大智若愚”的境界,即那种非自觉的、无深思熟虑可言的、高度服从的情性或自觉的境界。 在小说的整个叙述环境中,傻子二少爷似是始终处在一个被动的局外人的位置上,以一个傻子的眼光去看待和认识这个世界时,反而看清了事物的本质,看到了别人未看到的真相。而傻子又是历史与现实的参与者,当他真的参与到这个实际中的时候,对以下问题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土司制度的兴衰、藏汉文化的冲突和互补、土司父亲的慈爱与冷酷、哥哥被权利支配的灵魂的强大与软弱、母亲冷漠背后的孤寂、土司之间的利益之争和勾心斗角,等等。 傻子二少爷的悲剧性命运暗示了土司社会的命运。他的
重量级人物对阿来的中肯评价 我愿意做一个语言的信徒,就怕文字之神、语言之神不肯收我。 ——阿来 阿来在文坛一出现,就呈现出极高的写作起点,表现出一个“好作家”成熟的叙事品质,深邃的思想,独特的个性化语言、自由的文体和结构,令人瞩目。或者说,他是一位以能够改变人们阅读惯性、影响文学史发展惯性的重要作家的姿态出现在文坛的。他不排斥而且充分汲取外来文化和文学的养分,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行走方式,在自己喜欢的“大地的阶梯”上攀援。而阿来写作语言的个性化表现,让阿来的叙事文本,直接进入了文学的历史和现实。 作为一个作家,阿来认为写作中对语言的热爱和虔诚,敬畏和自律,是每一个杰出作家的自我诉求。一个写作者,如果对语言没有信徒般的情感和尊重,他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好作家,或者说,很难成为一个作家。在语言捕捉方面,阿来觉得我们都应该向汪曾祺先生学习,体悟他那种散漫的小说融散文式的结构精义。 阿来代表作:《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瞻对》,诗歌《梭磨河》,另有一些短篇小说集。
阿来的作品究竟如何呢?他的语言风格让我们感受到了哪些文学魅力呢?请看中国作家群体中几位重量级人物对其作的评价,不仅中肯,而且富于向上鼓舞的积极力量。这就是中国文学未来的希望吧! 陈晓明(北大中文系教授): 阿来一直在一个大的文明视角来看待故乡和生活,刻画鲜活人物。他具备理性的哲思,对生活以及文明历史,都有个人独特理解,深刻洞见的思考。 邱华栋: 阿来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多种文体的控制力和感觉,表现得都非常卓越,也给很多当代作家尤其是青年带来很大的启示。 潘凯雄(中国出版集团副总): 很多人都认为纯文学的作品传播不会太久,但阿来恰恰打破了这种绝对。《尘埃落定》20年的良好传播的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是经典的作品、优秀文学作品,同样能够得到很好的传播,同样能够有非常好的市场。 铁凝: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 蘑菇圈(节选) 阿来 蘑菇季快结束的时候,阿妈斯炯拿起手机,她想要给做州长的儿子胆巴打个电话。 她要告诉儿子,自己老了,腿不行了,明年不能再上山到自己的蘑菇圈跟前去了。 …… 第二天,丹雅就上门了。 丹雅带了好多好吃的东西,阿妈斯炯,我替胆巴哥哥看望你老人家来了。胆巴哥哥让我把你送到他那里去。 阿妈斯炯说,我哪里也不去,我只是再也不能去找我的蘑菇圈了。 丹雅说,那么让我替你来照顾那些蘑菇吧。 阿妈斯炯说,你怎么知道如何照顾那些蘑菇?你不会! 丹雅说,我会!不就是坐在它们身边,看它们如何从地下钻出来,就是耐心地看着它们慢慢现身吗? 阿妈斯炯说,哦,你不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 丹雅说,我知道,不就是看着它们出土的时候,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吗? 阿妈斯炯说,天哪,你怎么可能知道! 丹雅说,科技,你老人家明白吗?科学技术让我们知道所有我们想知道的事情。 阿妈斯炯说,你不可能知道。 丹雅问她,你想不想知道自己在蘑菇圈里的样子? 阿妈斯炯没有言语。 丹雅从包里拿出一台小摄像机,放在阿妈斯炯跟前。一按开关,那个监视屏上显出一片幽蓝。然后,阿妈斯炯的蘑菇圈在画面中出现了。先是一些模糊的影像。树,树间晃动的太阳光斑,然后,树下潮润的地面清晰地显现,枯叶,稀疏的草棵,苔藓,盘曲裸露的树根。阿妈斯炯认出来了,这的确是她的蘑菇圈。那块紧靠着最大栎树干的岩石,表面的苔藓因为她常常坐在上面而有些枯黄,现在,那个石头空着。一只鸟停在一只蘑菇上,它啄食几口,又抬起头来警觉地张望四周,又赶紧啄食几口。如是几次,那只鸟振翅飞走了。那只蘑菇的菌伞被啄去了一小半。 丹雅说,阿妈斯炯你眼神不好啊,这么大朵的蘑菇都没有采到。她指着画面,这里,这里,这么多蘑菇都没有看到,留给了野鸟。 阿妈斯炯微笑,那是我留给它们的。山上的东西,人要吃,鸟也要吃。 下一段视频中,阿妈斯炯出现了。那是雨后,树叶湿淋淋的。风吹过,树叶上的水滴簌簌落下。阿妈斯炯坐在石头上,一脸慈爱的表情,在她身子的四周,都是雨后刚出土的松茸。镜头中,阿妈斯炯无声地动着嘴巴,那是她在跟这些蘑菇说话。她说了许久的话。周围的蘑菇更多,更大了。她开始采摘,带着珍重的表情,小心翼翼地下手,把采摘下来的蘑菇轻手轻脚地装进筐里。临走,还用树叶和苔藓把那些刚刚露头的小蘑菇掩盖起来。 看着这些画面,阿妈斯炯出声了,她说,可爱的可爱的,可怜的可怜的这些小东西,这些小精灵。她说,你们这些可怜的可爱的小东西,阿妈斯炯不能再上山去看你们了。 丹雅说,胆巴工作忙,又是维稳,又是牧民定居,他接了你电话马上就让我来看你。 阿妈斯炯回过神来,问,咦!我的蘑菇圈怎么让你看见了?丹雅并不回答。她也不会告诉阿妈斯炯,公司怎么在阿妈斯炯随身的东西上装了GPS,定位了她的秘密。她也不会告诉阿妈斯炯,定位后,公司又在蘑菇圈安装了自然保护区用于拍摄野生动物的摄像机,只要有活物出现在镜头范围内,摄像机就会自动开始工作。 阿妈斯炯明白过来,你们找到我的蘑菇圈了,你们找到我的蘑菇圈了! 如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找不到的,阿妈斯炯,我们找到了。 阿妈斯炯心头溅起一点愤怒的火星,但那些火星刚刚闪出一点光亮就熄灭了。接踵而至的情绪也不是悲伤,而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种空洞的迷茫。她不说话,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只有丹雅在跟她说话。 丹雅说,我的公司不会动你那些蘑菇的,那些蘑菇换来的钱对我们公司没有什么用处。 丹雅说,我的公司只是借用一下你磨菇圈中的这些影像,让人们看到我们野外培植松茸成功,让他们看到野生状态下我公司种植的松茸怎样生长。 阿妈斯炯抬起头来,她的眼睛里失去了往日的亮光,她问,是为什么?
茅盾文学奖值得一读的10部作品,每部都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现在茅盾文学奖已经走过了30几个年头,一共颁发了9届,在这9届中,还是产生了许多非常不错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也都非常的有分量,那么下面就来带大家盘点一下,茅盾文学奖中10部值得一读的作品,看看你都读过了几部? 1、《芙蓉镇》 《芙蓉镇》是湖南著名作家古华的成名作,这部小说获得了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小说讲述了湖南一个名叫芙蓉镇的地方,通过女摊贩胡玉音、右派分子秦书田等人在"四清"到"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运动中的遭遇,对中国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近20年的历史做了严肃的回顾和深刻的反思。 可以说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这部作品不仅有着对于当地风土人情的描写,而且对于人性与历史,都有着深刻的反思,很是值得大家一读。 2、《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最为知名的作品,这部作品很好地传递了一种正确的价值观,人们通过阅读这部小说,可以明白很多的道理,尤其是一些人生的大道理。 路遥在这部作品中,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一个非常深沉的主题,那就是你应该如何活着?怎么活着? 一个人如果想要好好地活着,能够活得更好,那么唯一的方式,便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路遥也是凭借这部小说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3、《白鹿原》 《白鹿原》是陈忠实最为大家熟悉的作品,这部小说也是同样的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小说讲述了关中平原,一个名叫白鹿原的地方,在经历了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心理历程。作者把每一个人物,都刻画的非常深刻,让人读了之后,久久难以忘怀。 这部可以说是非常的厚重,陈忠实的文字功底,也是非常的深厚,他在这部小说里,把半个世纪的历史,都浓缩进了这部小说里。 4、《长恨歌》 《长恨歌》著名作家王安忆的作品,这部小说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王安忆被认为是张爱玲的传人,其实应当说她一点也不逊色于张爱玲,她的很多小说,那都写得非常出色,尤其是这部《长恨歌》,作者用一种平缓的语调,不紧不慢地把一个女人四十年的生命历程,展现的淋漓尽致。 王安忆的这部小说节奏非常的缓慢,但正是这一种缓慢,才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一个女人,渐渐衰老的过程,从这一点也同时说明,王安忆的文字功底,那是相当的扎实。 5、《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的成名作,据说这部小说,当年写好了之后,送去出版社,却是被无情的给退稿了,最后经过了种种困难,终于还是出版发行了。人们这才看到了一部惊艳的小说,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完美的小说,它无论是在写作上的创新,
阿来小说《天火》阅读 天火阿来 多吉手中一红一绿的两面小旗举起来,风立即把旗面展开,同时也标识出自身吹拂的方向。他挥动旗子的身姿像一个英武的将军。他口诵祷词。多吉是在呼唤火之神和风之神的名字。呼唤本尊山神的名字。他感觉到神灵们都听到了他的呼唤,来到了他头顶的天空,他的眉宇间掠过浅浅的一点笑意。 他在心里默念:“都说是新的世道,新的世道迎来了新的神,新的神教我们开会,新的神教我们读报纸,但是,所有护佑机村的旧的神啊,我晓得你们没有离开,你们看见,放牧的草坡因为这些疯长的灌木已经荒芜,你们知道,是到放一把火,烧掉这些灌木的时候了。” 神们好像有些抱怨之声。 多吉说:“新的神只管教我们晓得不懂的东西,却不管这些灌木疯长让牧草无处生长,让我们的牛羊无草可吃。” 他叹息了一声,好像听见天上也有回应他叹息的神秘声音,于是,他又深深叹息了一声,“所以,我这是代表乡亲们第二次求你们护佑。”他侧耳倾听一阵,好像听见了回答,至少,围在岩石下向上仰望的乡亲们从他的表情上看到,他好像是得到了神的回答。在机村,也只有他才能得到神的回答。因为,多吉一家,世代单传,是机村的巫师,是机村那些本土神与人群之间的灵媒。平常,他也只是机村一个卑微的农人。但在这个时候,他伛偻的腰背绷紧了,身材显得孔武有力。他混浊的眼睛放射出灼人的光芒,虬曲的胡须也像荆刺一样怒张开来。 “要是火镰第一下就打出了火花,”多吉提高了嗓门,“那就是你们同意了!”说完这句话,他跪下了,拿起早就备好的铁火镰,在石英石新开出的晶莹茬口上蒙上一层火绒草,然后深深地跪拜下去。 “神灵啊! 让铁与石相撞, 让铁与石撞出星光般的火星, 让火星燎原成势, 让火势顺风燃烧, 让风吹向树神厌弃的荆棘与灌丛, 让树神的乔木永远挺立, 山神!溪水神! 让烧荒后的土地来年牧草丰饶!” 唱颂的余音未尽,他手中的铁火镰已然与石英猛烈撞击。撞击处,一串火星迸裂而出,引燃了火绒草,就像是山神轻吸了一口烟斗,青烟袅袅地从火绒草中升起来,多吉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团升着青烟的火绒草,对着它轻轻而又深长地吹气,那些烟中便慢慢升起了一丛幽蓝的火苗。他向着人群举起这团火,人群中发出齐声的赞叹。他捧着这丛火苗,通了灵的身躯,从一丈多高的岩石顶端轻盈地一跃而下,把早已备好的火堆引燃。 几十支火把从神态激越庄严的人们手中伸向火堆,引燃后又被高高举起。多吉细细观察一阵,火苗斜着呼呼飘动,标示出风向依然吹向面南朝阳,因杂灌与棘丛疯长而陷于荒芜的草坡,他对着望向他的人群点了点头,说:“开始吧。” 举着火把的人们便沿着冰封峡谷的上下跑去。 每个人跑出一段,便将火把伸向这秋冬之交干透的草丛与灌木,一片烟障席地而起,然后,风吹拂着火苗,从草坡下边,从冰封溪流边开始,升腾而上。剩下的人们,都手持扑火工具,警惕着风,怕它突然转向,把火带向北坡的森林。虽然,沟底封冻溪流形成的宽阔冰
阿来《马车夫》 高考文学类文本阅读练习及答案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4小题,16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面小题。 马车夫 阿来 这个人身材瘦小,脸上还布满了天花留下的斑斑印迹,但他却是机村最好的骑手,他骑在马上,就跟长在马背上一样自在稳当。机村人认为,这样的人用马眼看去,会有非常特别的地方。 试驾马车那一天,麻子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他骑着一匹马徘徊在热闹的圈子外边。人们扎成一圈,看村里的男子汉们费尽力气想把青鬃马塞进两根车辕之间,用那些复杂的绊索使它就范。折腾了很长时间,他们也没有能给青鬃马套上那些复杂的绊索。青鬃马又踢又咬。 人们这才把眼光转向了勒马站在圈子之外的麻子。 在众人的注视下,他脸上那些麻坑一个个红了。他抬腿下了马背,慢慢走到青鬃马跟前。他说:“吁——”青鬃马竖起的尾巴就慢慢垂下了。他伸出手,轻拍一下青鬃马的脖子,挠了挠马正呼出滚烫气息的鼻翼,牲口就安静下来了。这个家伙,脸上带着沉溺进了某种奇异梦境的浅浅笑容,开始嘀嘀咕咕地对马说话,马就定了身站在两根结实的车辕中间,任随麻子给它套上肩轭和复杂的绊索。中辕驾好了,两匹边辕也驾好了。 人群安静下来。
麻子牵着青鬃马迈开了最初的两步。这两步,只是把套在马身上那些复杂的绊索绷紧了。麻子又领着三匹马迈出了小小的一步。这回,马车的车轮缓缓地转动了一点。但是,当麻子停下了步子,轮子又转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走啊,麻子!”人们着急了。 麻子笑了,细眼里放出锐利的亮光,他连着走了几步。轮子就转了大半圈。轮箍和轮轴互相摩擦,发出了旋转着的轮子必然会发出的声音。马也像一只鸟,有点胆怯又有点兴奋地要初试啼声,刚叫出半声就停住了。 马也竖起了耳朵,谛听身后那陌生的声音。 他又引领着马迈开了步子。 三匹马,青鬃马居中,两匹黑马分行两边,牵引着马车继续向前。转动的车轮终于发出了完整的声音: 叽——吭! 前半声小心翼翼,后半声理直气壮。 那声音如此令人振奋,三匹马不再要驭手引领,就伸长脖颈,耸起肩胛,奋力前行了。 麻子从车头前闪开,在车侧紧跑几步,腾身而起,安坐在了驭手座上,取过竖在车辕上的鞭子,凌空一抽,马车就蹿出了广场,向着村外的大道飞驰起来。 从此,一直蜗行于机村的时间也像给装上了飞快旋转的车轮,转眼之间就快得像是射出的箭矢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