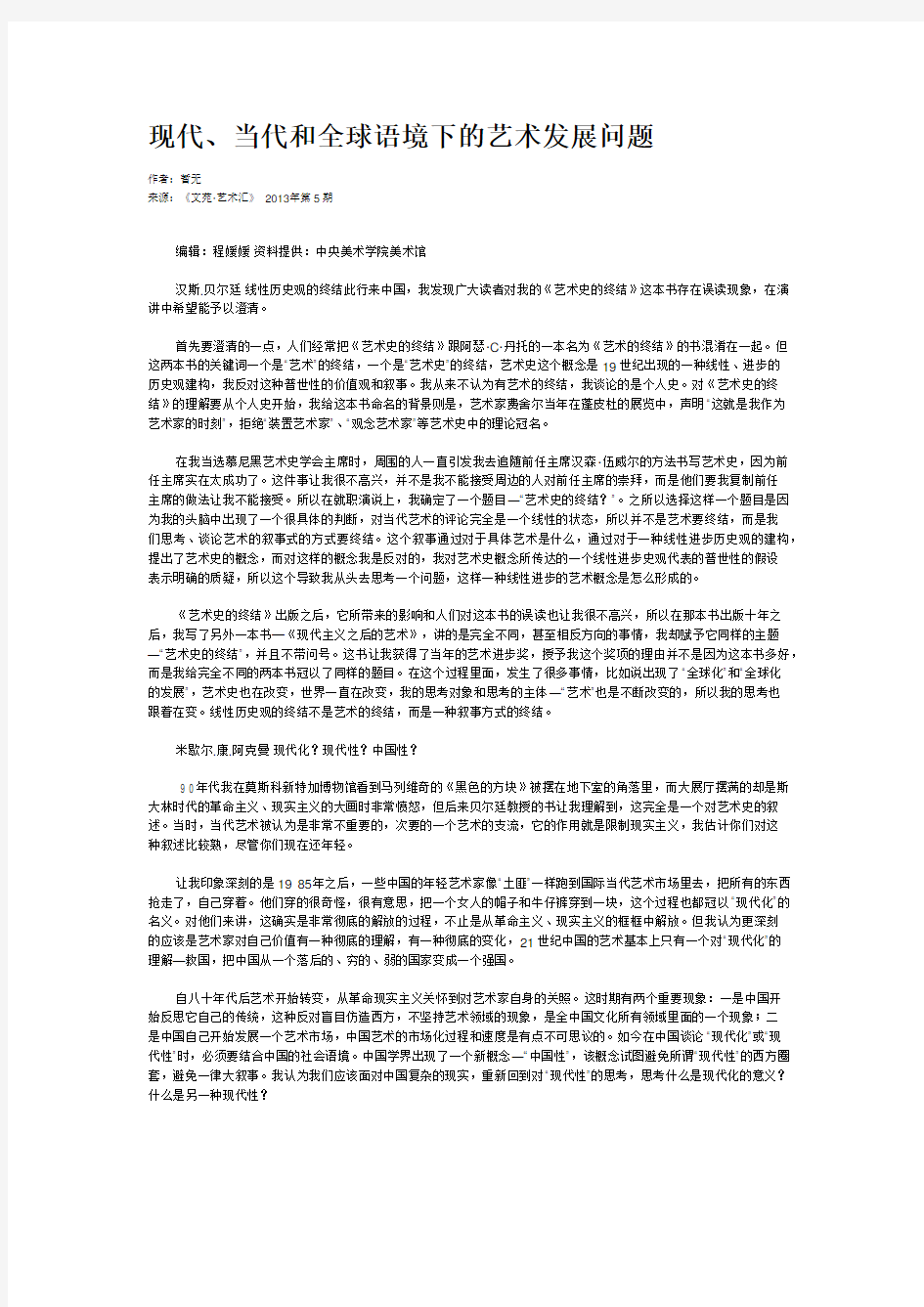

现代、当代和全球语境下的艺术发展问题
作者:暂无
来源:《文苑·艺术汇》 2013年第5期
编辑:程媛媛资料提供: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汉斯.贝尔廷线性历史观的终结此行来中国,我发现广大读者对我的《艺术史的终结》这本书存在误读现象,在演
讲中希望能予以澄清。
首先要澄清的一点,人们经常把《艺术史的终结》跟阿瑟·C·丹托的一本名为《艺术的终结》的书混淆在一起。但
这两本书的关键词一个是“艺术”的终结,一个是“艺术史”的终结,艺术史这个概念是19世纪出现的一种线性、进步的
历史观建构,我反对这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和叙事。我从来不认为有艺术的终结,我谈论的是个人史。对《艺术史的终结》的理解要从个人史开始,我给这本书命名的背景则是,艺术家费舍尔当年在蓬皮杜的展览中,声明“这就是我作为
艺术家的时刻”,拒绝“装置艺术家”、“观念艺术家”等艺术史中的理论冠名。
在我当选慕尼黑艺术史学会主席时,周围的人一直引发我去追随前任主席汉森·伍威尔的方法书写艺术史,因为前
任主席实在太成功了。这件事让我很不高兴,并不是我不能接受周边的人对前任主席的崇拜,而是他们要我复制前任
主席的做法让我不能接受。所以在就职演说上,我确定了一个题目—“艺术史的终结?”。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是因
为我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个很具体的判断,对当代艺术的评论完全是一个线性的状态,所以并不是艺术要终结,而是我
们思考、谈论艺术的叙事式的方式要终结。这个叙事通过对于具体艺术是什么,通过对于一种线性进步历史观的建构,提出了艺术史的概念,而对这样的概念我是反对的,我对艺术史概念所传达的一个线性进步史观代表的普世性的假设
表示明确的质疑,所以这个导致我从头去思考一个问题,这样一种线性进步的艺术概念是怎么形成的。
《艺术史的终结》出版之后,它所带来的影响和人们对这本书的误读也让我很不高兴,所以在那本书出版十年之后,我写了另外一本书—《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讲的是完全不同,甚至相反方向的事情,我却赋予它同样的主题—“艺术史的终结”,并且不带问号。这书让我获得了当年的艺术进步奖,授予我这个奖项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这本书多好,而是我给完全不同的两本书冠以了同样的题目。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出现了“全球化”和“全球化
的发展”,艺术史也在改变,世界一直在改变,我的思考对象和思考的主体—“艺术”也是不断改变的,所以我的思考也
跟着在变。线性历史观的终结不是艺术的终结,而是一种叙事方式的终结。
米歇尔.康.阿克曼现代化?现代性?中国性?
9 0年代我在莫斯科新特加博物馆看到马列维奇的《黑色的方块》被摆在地下室的角落里,而大展厅摆满的却是斯大林时代的革命主义、现实主义的大画时非常愤怒,但后来贝尔廷教授的书让我理解到,这完全是一个对艺术史的叙述。当时,当代艺术被认为是非常不重要的,次要的一个艺术的支流,它的作用就是限制现实主义,我估计你们对这
种叙述比较熟,尽管你们现在还年轻。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19 85年之后,一些中国的年轻艺术家像“土匪”一样跑到国际当代艺术市场里去,把所有的东西抢走了,自己穿着。他们穿的很奇怪,很有意思,把一个女人的帽子和牛仔裤穿到一块,这个过程也都冠以“现代化”的
名义。对他们来讲,这确实是非常彻底的解放的过程,不止是从革命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框中解放。但我认为更深刻
的应该是艺术家对自己价值有一种彻底的理解,有一种彻底的变化,21世纪中国的艺术基本上只有一个对“现代化”的
理解—救国,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穷的、弱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国。
自八十年代后艺术开始转变,从革命现实主义关怀到对艺术家自身的关照。这时期有两个重要现象:一是中国开
始反思它自己的传统,这种反对盲目仿造西方,不坚持艺术领域的现象,是全中国文化所有领域里面的一个现象;二
是中国自己开始发展一个艺术市场,中国艺术的市场化过程和速度是有点不可思议的。如今在中国谈论“现代化”或“现
代性”时,必须要结合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国学界出现了一个新概念—“中国性”,该概念试图避免所谓“现代性”的西方圈套,避免一律大叙事。我认为我们应该面对中国复杂的现实,重新回到对“现代性”的思考,思考什么是现代化的意义?
什么是另一种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