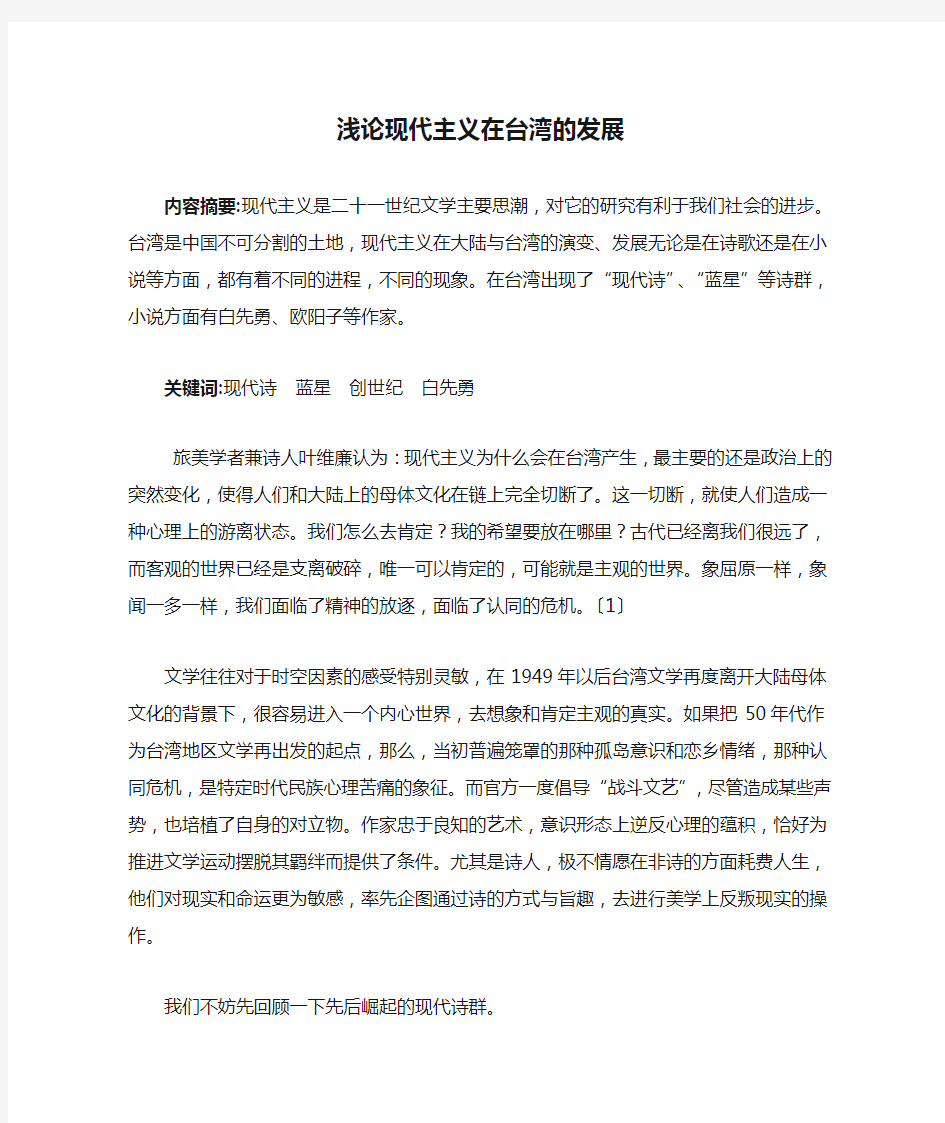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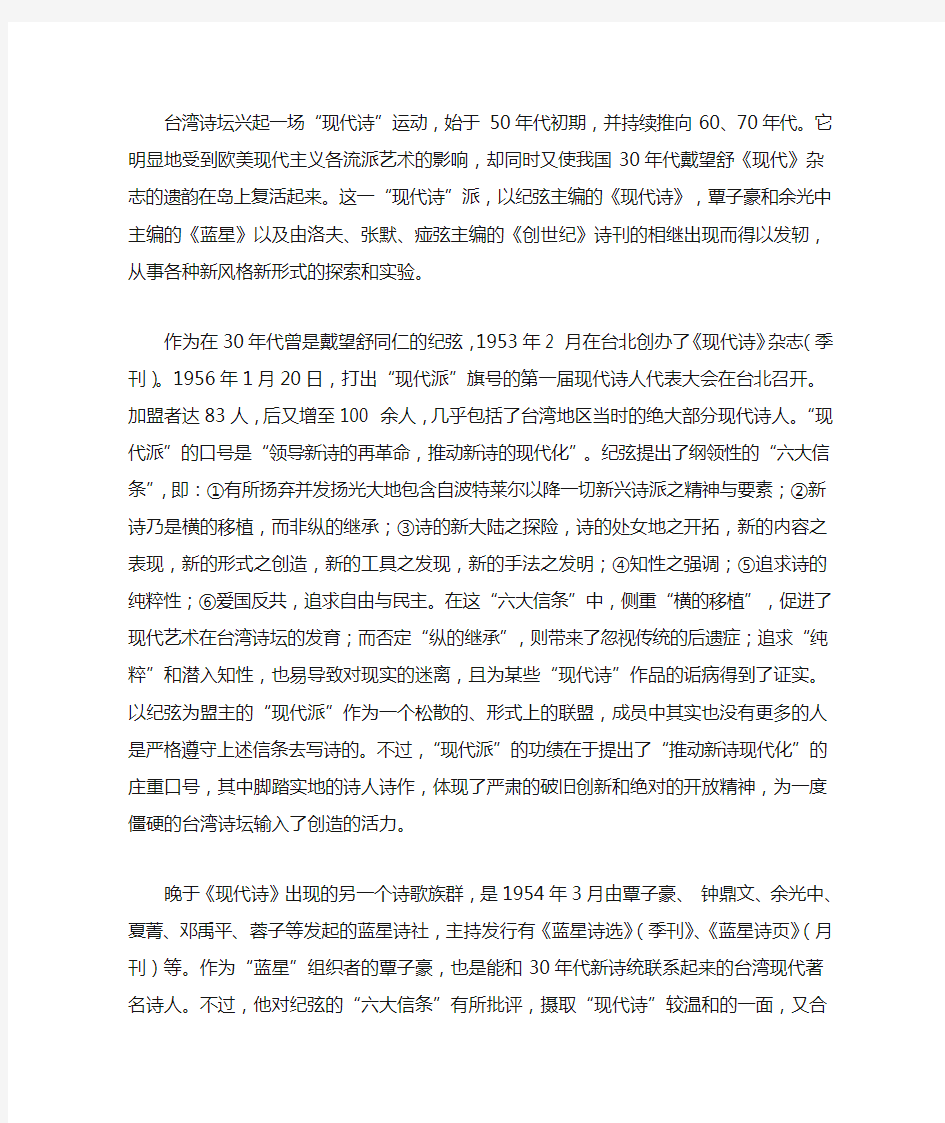
浅论现代主义在台湾的发展
内容摘要:现代主义是二十一世纪文学主要思潮,对它的研究有利于我们社会的进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土地,现代主义在大陆与台湾的演变、发展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小说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进程,不同的现象。在台湾出现了“现代诗”、“蓝星”等诗群,小说方面有白先勇、欧阳子等作家。
关键词:现代诗蓝星创世纪白先勇
旅美学者兼诗人叶维廉认为:现代主义为什么会在台湾产生,最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突然变化,使得人们和大陆上的母体文化在链上完全切断了。这一切断,就使人们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游离状态。我们怎么去肯定?我的希望要放在哪里?古代已经离我们很远了,而客观的世界已经是支离破碎,唯一可以肯定的,可能就是主观的世界。象屈原一样,象闻一多一样,我们面临了精神的放逐,面临了认同的危机。〔1〕
文学往往对于时空因素的感受特别灵敏,在1949年以后台湾文学再度离开大陆母体文化的背景下,很容易进入一个内心世界,去想象和肯定主观的真实。如果把50年代作为台湾地区文学再出发的起点,那么,当初普遍笼罩的那种孤岛意识和恋乡情绪,那种认同危机,是特定时代民族心理苦痛的象征。而官方一度倡导“战斗文艺”,尽管造成某些声势,也培植了自身的对立物。作家忠于良知的艺术,意识形态上逆反心理的蕴积,恰好为推进文学运动摆脱其羁绊而提供了条件。尤其是诗人,极不情愿在非诗的方面耗费人生,他们对现实和命运更为敏感,率先企图通过诗的方式与旨趣,去进行美学上反叛现实的操作。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先后崛起的现代诗群。
台湾诗坛兴起一场“现代诗”运动,始于50年代初期,并持续推向60、70年代。它明显地受到欧美现代主义各流派艺术的影响,却同时又使我国30年代戴望舒《现代》杂志的遗韵在岛上复活起来。这一“现代诗”派,以纪弦主编的《现代诗》,覃子豪和余光中主编的《蓝星》以及由洛夫、张默、痖弦主编的《创世纪》诗刊的相继出现而得以发轫,从事各种新风格新形式的探索和实验。
作为在30年代曾是戴望舒同仁的纪弦,1953年2 月在台北创办了《现代诗》杂志(季刊)。1956年1月20日,打出“现代派”旗号的第一届现代诗人代表大会在台北召开。加盟者达83人,后又增至100 余人,几乎包括了台湾地区当时的绝大部分现代诗人。“现代派”的口号是“领导新诗的再革命,推动新诗的现代化”。纪弦提出了纲领性的“六大信条”,即:①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含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②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③诗的新大陆之探险,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现,新的手法之发明;④知性之强调;⑤追求诗的纯粹性;
⑥爱国反共,追求自由与民主。在这“六大信条”中,侧重“横的移植”,促进了现代艺术在台湾诗坛的发育;而否定“纵的继承”,则带来了忽视传统的后遗症;追求“纯粹”和潜入知性,也易导致对现实的迷离,且为某些“现代诗”作品的诟病得到了证实。以纪弦为盟主的“现代派”作为一个松散的、形式上的联盟,成员中其实也没有更多的人是严格遵守上述信条去写诗的。不过,“现代派”的功绩在于提出了“推动新诗现代化”的庄重口号,其中脚踏实地的诗人诗作,体现了严肃的破旧创新和绝对的开放精神,为一度僵硬的台湾诗坛输入了创造的活力。
晚于《现代诗》出现的另一个诗歌族群,是1954年3月由覃子豪、钟鼎文、余光中、夏菁、邓禹平、蓉子等发起的蓝星诗社,主持发行有《蓝星诗选》(季刊》、《蓝星诗页》(月刊)等。作为“蓝星”组织者的覃子豪,也是能和30年代新诗统联系起来的台湾现代著名诗人。不过,他对纪弦的“六大信条”有所批评,摄取“现代诗”较温和的一面,又合并大陆“新月派”的某些风格,提出“整理出一个新的秩序”的理论主张。覃子豪认为发展新诗的“六项正确原则”是:①艺术的表现离不开人生,注视人生本身及人生事象,表现一种崭新人生境界;②在作者和读者两座悬崖之间,寻得两者都能望见的焦点;③重视实质及表现的完美;④寻求诗的思想根源;⑤从准确中求新的出现;⑥风格是自我创造的完成。“蓝星”同样是一个松散的诗歌社团,除诗风大致共同倾向于抒情外,其成员在精神和风格上亦存差异,部分受欧美诗的影响也颇深。诚如余光中在其英译选本《中国新诗》的序言中所说:“他们(蓝星同仁)的作品不比现代派诗人的难懂,且显示各种不同的外来影响。夏菁深受荻瑾生、弗洛斯特与其他美国诗人的影响,吴望尧表现了由中国传统抒情诗到达达主义的各个风格,黄用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激情而施以古典主义抑制,覃子豪的句法基本上是纯中国的,但对题材的处理则倾向于法国的象征主义……罗门则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了天花乱坠的理想主义。”“蓝星”诗社后因主将覃子豪谢世,在罗门、蓉子夫妇编完《蓝星1964》后宣告解散,乃至80年代初又重新恢复诗社活动。
把台湾的现代诗运动持续推向前进的有韧劲、有实绩的社团,当推纵横诗坛四十年的“创世纪”诗社。《创世纪》创刊于1954年10月,由洛夫、张默主编,第二期起又有痖弦加入,被戏称为创世纪“三驾马车”。在它宣告为“试验期”的头五年,提供现代诗派的“新民族诗型”,用洛夫的话来说,就是:“新民族诗型的基本要素有二,一是艺术的——非纯理性的阐发,亦非纯情绪的直陈,而是美学上直觉的意象之表现,我们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且必须是精粹的,诗的,而不是散文的。二是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字之特性,以表现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在将近十年的“创造期”里,他们基于艺术贫血和渴求新的表现手法,接纳世界性的现代主义,求助于西方的缪斯,强调“超现实性”、“反理性”和以“直觉”与“暗示”为前提的语言及技巧的多种实验。70年代起,“创世纪”又迈入第三阶段即自称的“自觉期”,由回顾、批评、反省而形成一种审慎的自我评估,如同在该刊一篇题为《一颗不死的麦子》的社论中强调的:“我们在批判与吸收了中西文学传统之后,将努力于一种新的民族风格之塑造,唱出真正属于我们这一时代的声音。”1988年8月出版的《创世纪诗杂志》73、74期合订本上,他们又经过检视和调适,由洛夫在《建立大中国诗观的沉思》的长篇论文中,提出“追求诗的现代化”和“开创诗的新传统”两项建议。文中强调:“我们要创造的现代诗不只是新文学史上一次阶段性的名词,而是以现代为貌,以中国为神的诗。同时,一个现代中国诗人必须站在纵的(传统)和横的(世界)坐标点上,去感受,去体验,去思考近百年来中国人泅过血泪的时空,在历史中承受无穷尽的捶击与磨难所激发的悲剧精神,以及由悲剧精神所衍生的批评精神,并进而去探索整个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意义,然后通过现代美学规范下的语言形式,以展现个人风格和地方风格的特殊性,表现大中华文化心理结构下的民族性,和以人道主义为依归的世界性。”至此,“创世纪”的路线遂调整到“创造现代化的中国诗”的界标上来。
“现代诗”、“蓝星”和“创世纪”是台湾当代文坛上三个最有代表性的现代诗社,前二者皆为松散的同盟,后者聚而不散,并陆续吸收了前二者的诗人及
新秀壮大阵营。尽管它们之间在诗学观念上不无差异,但作为现代诗群,有着一些共同取向和特征。这主要是:由于在台湾地区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潮难以谐和,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时价值脱节,那种难以排遣的惶恐和困惑、失落和忧患,使不少诗在一种隔绝状态中走入个人的世界、感官经验的世界、潜意识和梦的世界;对于旨在表现人生、探索人性的“知性”之普遍强调与追求,竭力超越单纯而即兴的抒情,进入富于冷静观照或是多元表现的境地;擅长于运用暗示和象征,致使作品的主题含蓄得多,层次也深浅有致;普遍地重视结构与语言的重建,为了加强语言的效果化和感性化,不但用文字的本义,更注意用文字的引申义、联想、意象、符征、歧义、张力等等,在视觉和听觉上构成感知的交融存在和立体效应。现代诗派曾有过“失根的移植”现象,经过反省与调整,被视作必要的阶段和过程,对于丰富诗质的密度和拓宽艺术的视野亦不无益处,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现代诗群曾被视为“迷途的羔羊”而遭到过种种驳难。但今天若以宽容精神历史地、公允地看,正由于几大诗社的冲击与抗争,才出现了台湾地区新诗的中兴,也孕育了后来众多的星辰。“浪子”和“浪行”是诗歌发展过程中一种开阔视野、重新认识自身的必要阶段。“横的移植”作为不无偏激、同时又不无保留的实践〔2〕处理得法,有可能以较深刻的批判意识去审视古典诗学遗产,且以现代人科学和民主的眼光与心境进行思考、决定取舍,也有利于面对古典的繁富芜杂以更好地实施“纵的继承”。显然,这和某些批评者心目中“浪子回头”、“复归传统”的武断是两回事。开放的文学观,该是既有庄生之梦,又有罗丹之思,在一块复杂的大地上播下多种话语的种子,并不断进行土壤改良,使之长出更健旺的美学之树。
台湾地区的现代主义文学,以诗歌为发端,以小说的随行而进入盛期。
60年代初,台湾社会转型,西风东渐,经济起飞,传统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受到怀疑和冲击。孤悬海外,不仅使外省的、也使本土的作家增长着悲苦寂寥的思绪,并对文学界的一些流行作品深表失望。白先勇指出,一些作家“笔下的人物大多与现实脱节,布局情节老套公式化,故事的主人翁不管如何饱尝流放的苦痛,总是会重临故土,与大陆上的家人团圆结局。这些作品满注思乡情怀,但这种悲伤的感受老是陈腐俗套,了无新意。”〔3〕当时的文学青年更渴望求新求变,寻找文学的出路。诚如余光中所追述,他们“甚至对一切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的文学都起了反感,至少起了怀疑。余下来的一条路,似乎就只有向内走,走入个人的世界,感官经验的世界,潜意识和梦的世界。弗洛伊德的泛性说和心理分析,意识流手法的小说,反理性的诗等等,乃成为年轻作者刻意追摹的对象。”〔4〕
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夏济安带出的一帮弟子,成为台湾现代派小说创作最初的中坚。1960年3月5日创刊的《现代文学》,由白先勇牵头,是提倡纯艺术和推崇现代派重要的文学园地。这批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声称:“我们打算分期有系统地介绍翻译西方现代艺术学派和潮流、批评和思想,并尽可能选择其代表作品。我们如此做,毫不表示我们对外国艺术的偏爱,仅仅依据‘他山之石’之进步原则”;“我们感于旧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于表现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艺术情感,所以,我们决定试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5〕在“现代”的迷惑之下,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七等生、丛甦等等一批年轻的小说作家,仿效陌生化的手法,将自己对现实世界深深的怀疑与思考,溶入了求变创新的艺术形式之中。
尽管打出“现代派”的旗号,但在实践上,这些追求现代取向的小说家的文学主张与创作风格却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个小说家,也有理论上与实践上自相矛盾的情况,或者前后之间的某些变化。总体上看,大致有三种情状:一是取法传统母题,以现实主义为主,吸收西方现代派的形式、风格和技巧,探索“将西式的技巧和中式的题材熔于一炉”〔6〕的道路。
二是引进外来主题,冲击和突破传统文化禁忌与创作方法,用现代感觉观照或折射台湾社会现实,特别是表现都市人的灵魂和心理。
三是对西方现代派模仿多于借鉴,形式重于内容,乃至笨拙地套用和夸大,猎奇般地渲染或移植异域风物,既与台湾地区的社会情况、也与中国人的生命情调相脱节。显然,这是属于低劣的末路。
在台湾地区小说创作的现代主义运作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一些作家在协调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时的矛盾、困惑的心情,即所谓“既爱犹恨,说恨还爱”的情结:对传统文化持一种骄傲而又鄙夷的目光,对西方文明取一种既恨(霸权、制华)而又爱其输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态度。他们在两难的困境中彷徨和摸索,不满于当时恶劣和俗陋的文化生态环境,又以引进现代主义企图达到提升当地文学艺术的品质的目的。其中一部分真诚的小说作品,在采取诸如象征、戏谑、反讽、反身自涉、认知置疑、符征与符旨分离等等策略中,寻找着既能满足表达对现实与人生的看法的创作欲望,又可以在别人感到陌生乃至艰涩、却不致于干犯禁忌的形式中,道出作家心中的块垒。
正因为如此,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误读或批评的错位难免会发生。如海峡两岸的文学批评中,迄今仍流行“恶性西化”的字眼。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既属“西化”,有“恶性”的,难道还有“良性”的吗?我们尊重并主张表现批评家个性的话语,但需以谋求科学性而减少随意性为前提,在宽容的学理指导下确定客观公正的批评取向。又譬如,批评界往往习惯于“划线列派”,而且一旦某位作家被划为某派,似乎就被看死了。实际上,作家作品是复杂的,且常常变动不居。我们可以大致上有个总体倾向的判断,但一进入文本研究,就要看到复杂的、交叉的现象。拿白先勇来说,不少著述将他列入“现代派”对待。事实上,白先勇当初以“反传统”崛起,但他的《台北人》、《纽约客》等系列小说,寻求的仍是与中国人的感知传统的汇通,并与审美的、道德的、历史的以及当代台湾生活现实相联系。他多取传统写实显意的笔法,甚至不规避直白。读者只要看一下《谪仙记》的诗题“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看一下《台北人》的诗题“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看一下《永远的尹雪艳》里那种“妩媚无愁”的外在形象和那种因“隔离”的阻绝而永远不得结合的内在意蕴的非仙非人的伤感,就不难明白,白先勇当初的“现代小说”,多半乃“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隔绝之痛,是对一种文化的无法挽回的万古忧愁,技巧上中西无碍地博采众长而更圆熟罢了。再以王祯和为例,一般被视作“乡土派”小说家,但他的代表作《嫁妆一牛车》,虽属乡土题材,恰恰是用了绝对现代派的手法,取“多重声音”的叙述策略。作品中那个变态的、令人又好气又好笑的叙事者的心理变异,叙述方式上既直接又曲折的反复运作,叙述语调上间杂着土话脏话的非高雅化的那种怪诞,合起来,造成一种对人性尊严嘲弄的“震颤”的艺术效果。它无疑运用了现代派常见的以大胆逼视生存状态和心理体验而呈示人类经验的吊诡原则,反映了台湾人的处境和在强权势力下不得不采取自嘲的生存策略。
相对而言,七等生、王文兴、欧阳子、丛甦、林怀民等人,是台湾当代文学
中较正牌的现代主义小说家。欧阳子的《那长发的女孩》、《秋时》、《墙》等小说,企图以西方取向的现代认知方式去观照发生于少女、少妇和中年妇女之间在性爱问题上的变态心理与畸形恋情,其偏颇在于以纯粹的两性关系掩盖了人的更为本质的生命活动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却也从另一个层面表达了主体认知的局限和人间真相不可穿透的无奈。七等生往往把视点落在“现代人”病态的心理现实上,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感与疏离感成了他小说中的常见主题。他的名篇《我爱黑眼珠》,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荒唐:一场洪水把主人公索龙第和其妻晴子分隔异处,他却是救出了一个“黑色眼睛”的妓女而置对岸千呼万唤的妻子于不顾,并出于本能冲动与“黑眼睛”缠绵起来,直到洪水消退、妓女离去,他才想起还有一个被洪水冲走而自己寻救乏力的妻子。作家曾自白,之所以要制造如此非理性的、超验的寓言,是为了“把现实的美恶的区别观念完全抛弃,让良知和自由的灵魂展现出来”,以便让弗洛伊德式的“原我”有一个“争取活动的时空”〔7〕。看来,传统的道德评判难以规范此类不守规矩的作品,我们只能从这些又自私又不自私、行为怪僻又不失生命力真实的小人物那里,感受到畸形发展的都市社会挤逼下凡夫俗子们的声声叹息。丛甦的成名作《盲猎》,制造了一个通体的象征氛围,一个浑然圆融的梦魇世界。猎手们在黑森林中的“盲猎”,象征着人类自我挣扎的盲目与徒然;那“很久很久”,那“白眉白须”,亦喻指人类自身生存的目的与意义的不可企及性,似乎又是古老而永恒的话题。作家显然接受了现代派的怀疑精神,步入卡夫卡笔下的那种“城堡”。王文兴写了整整七年的长篇代表作《家变》,被一些批评家视作表现了“西化”与“孝道”的伦理冲突,事实上,作家以其怪僻奇诡的语言实验,讨论了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的父与子的问题,具有反省的意义。至于更年轻的作家林怀民,在《辞乡》、《蝉》等作品中,运用通感、意识流及蒙太奇等手法去刻画人物形象,揭示内心世界,表现台湾地区“失落一代”的枯寂虚无和精神漂泊。
近40年来,台湾地区的诗歌和小说一直在族群崛起、争鸣不已中运行。先后发生的和反复纠缠的诸如西化/回归、主流/非主流、晦涩/明朗、重现实/超现实、乡土/现代、主观/即物、横的移植/纵的继承等等的二元对立和二值判断,不妨留给文学史家去考证和厘清。诗学(此指广义的文艺理论)研究自然要注意论争的背景,但更为重要的是,从批评和创作中发掘那些对于中国当代诗学的推进富有建设性的东西,考察薪火相传之道,寻找那些文学垦地上洗去幽暗色泽而髹之以光彩涵容的新绿新穗,而不是在族群的高下文野上争执不休。
参考文献:
〔1〕杜甫发.《现代经验的反省——叶维廉答客问》,《南洋商报》“文林”版,1981年7月.
〔2〕纪弦致吴奔星(大陆教授、诗人)函.“你说我又回归传统了,这话不对,我永远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但我是中国的现代主义者,而非英美的或法国的。”.
〔3〕白先勇.《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
〔4〕余光中.《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总序》,台北巨人出版社1972年1
月初版.
〔5〕《现代文学》杂志创刊号“发刊词”,1960年3月5 日版.
〔6〕李欧梵.《台湾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
〔7〕七等生.《放生鼠·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