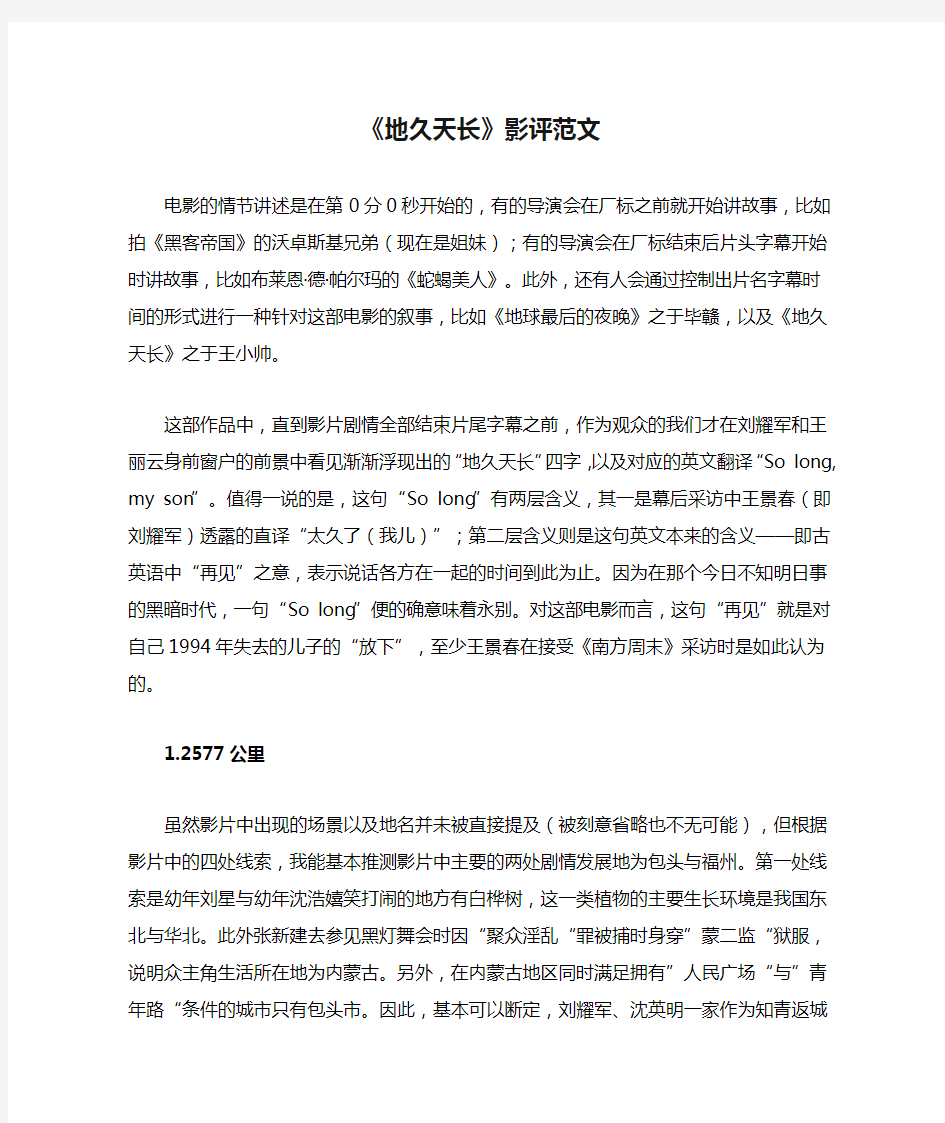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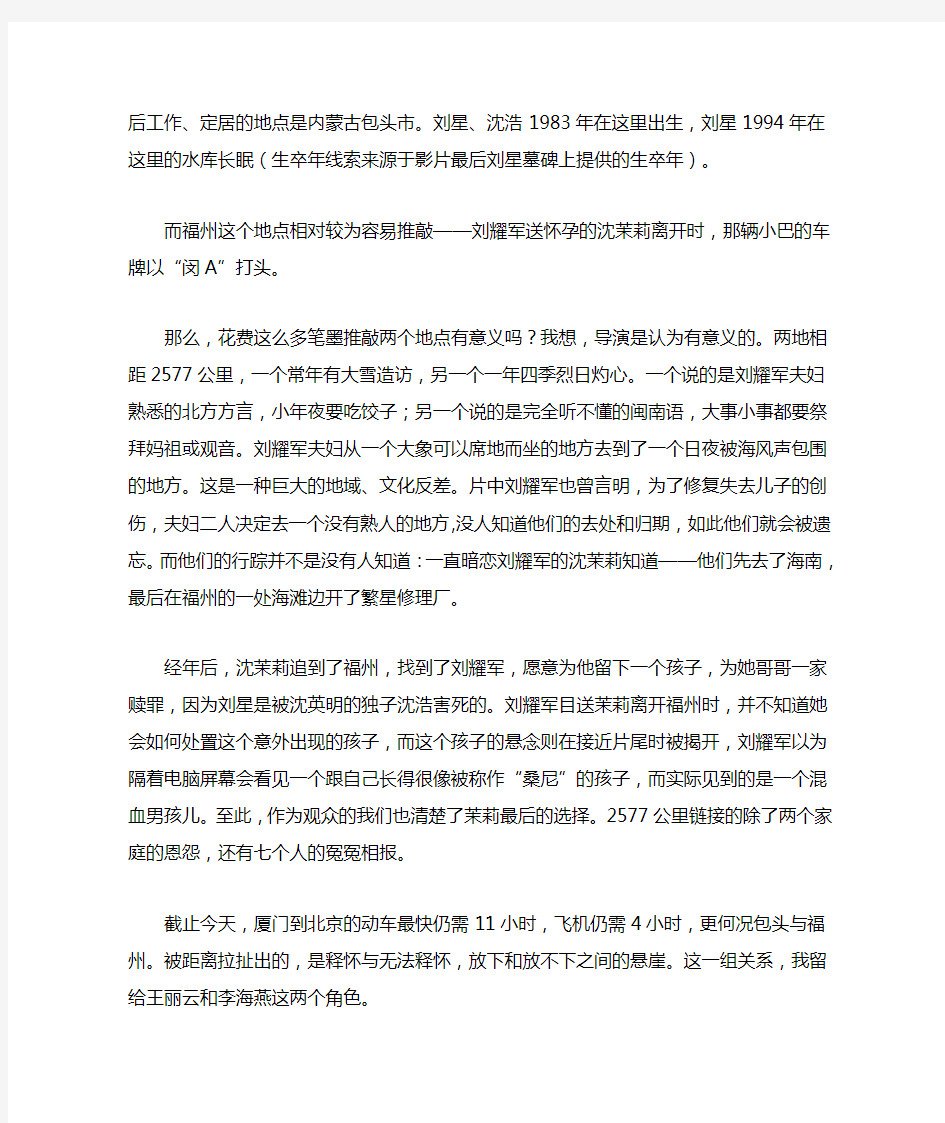
《地久天长》影评范文
电影的情节讲述是在第0分0秒开始的,有的导演会在厂标之前就开始讲故事,比如拍《黑客帝国》的沃卓斯基兄弟(现在是姐妹);有的导演会在厂标结束后片头字幕开始时讲故事,比如布莱恩·德·帕尔玛的《蛇蝎美人》。此外,还有人会通过控制出片名字幕时间的形式进行一种针对这部电影的叙事,比如《地球最后的夜晚》之于毕赣,以及《地久天长》之于王小帅。
这部作品中,直到影片剧情全部结束片尾字幕之前,作为观众的我们才在刘耀军和王丽云身前窗户的前景中看见渐渐浮现出的“地久天长”四字,以及对应的英文翻译“So long, my son”。值得一说的是,这句“So long”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幕后采访中王景春(即刘耀军)透露的直译“太久了(我儿)”;第二层含义则是这句英文本来的含义——即古英语中“再见”之意,表示说话各方在一起的时间到此为止。因为在那个今日不知明日事的黑暗时代,一句“So long”便的确意味着永别。对这部电影而言,这句“再见”就是对自己1994年失去的儿子的“放下”,至少王景春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是如此认为的。
1.2577公里
虽然影片中出现的场景以及地名并未被直接提及(被刻意省略也不无可能),但根据影片中的四处线索,我能基本推测影片中主要的两处剧情发展地为包头与福州。第一处线索是幼年刘星与幼年沈浩嬉笑打闹的地方有白桦树,这一类植物的主要生长环境是我国东北与华北。此外张新建去参见黑灯舞会时因“聚众淫乱“罪被捕时身穿”蒙二监“狱服,说明众主角生活所在地为内蒙古。另外,在内蒙古地区同时满足拥有”人民广场“与”青年路“条件的城市只有包头市。因此,基本可以断定,刘耀军、沈英明一家作为知青返城后工作、定居的地点是内蒙古包头市。刘星、沈浩1983年在这里出生,刘星1994年在这里的水库长眠(生卒年线索来源于影片最后刘星墓碑上提供的生卒年)。
而福州这个地点相对较为容易推敲——刘耀军送怀孕的沈茉莉离开时,那辆小巴的车牌以“闵A”打头。
那么,花费这么多笔墨推敲两个地点有意义吗?我想,导演是认为有意义的。两地相距2577公里,一个常年有大雪造访,另一个一年四季烈日灼心。一个说的是刘耀军夫妇熟悉的北方方言,小年夜要吃饺子;另一个说的是完全听不懂的闽南语,大事小事都要祭拜妈祖或观音。刘耀军夫妇从一个大象可以席地而坐的地方去到了一个日夜被海风声包围的地方。这是一种巨大的地域、文化反差。片中刘耀军也曾言明,为了修复失去儿子的创伤,夫妇二人决定去一个没有熟人的地方,没人知道他们的去处和归期,如此他们就会被遗忘。而他们的行踪并不是没有人知
道:一直暗恋刘耀军的沈茉莉知道——他们先去了海南,最后在福州的一处海滩边开了繁星修理厂。
经年后,沈茉莉追到了福州,找到了刘耀军,愿意为他留下一个孩子,为她哥哥一家赎罪,因为刘星是被沈英明的独子沈浩害死的。刘耀军目送茉莉离开福州时,并不知道她会如何处置这个意外出现的孩子,而这个孩子的悬念则在接近片尾时被揭开,刘耀军以为隔着电脑屏幕会看见一个跟自己长得很像被称作“桑尼”的孩子,而实际见到的是一个混血男孩儿。至此,作为观众的我们也清楚了茉莉最后的选择。2577公里链接的除了两个家庭的恩怨,还有七个人的冤冤相报。
截止今天,厦门到北京的动车最快仍需11小时,飞机仍需4小时,更何况包头与福州。被距离拉扯出的,是释怀与无法释怀,放下和放不下之间的悬崖。这一组关系,我留给王丽云和李海燕这两个角色。
王丽云,刘耀军妻子,刘星的母亲,在整个电影近四十年的跨度中需要承受最多的痛苦。而李海燕可以说为这份痛苦提供了最大的比重。李海燕升任计生办主任时王丽云刚得知自己有了第二胎,彼时距离沈浩带刘星去那个致命的水库已经不远。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李海燕带着相关工作人员逼迫王丽云打胎,术中大出血,此后王丽云失去了生育能力。这是一种生活对他们无情的剥夺,而作为施害方的李海燕还在被他人安慰,借口是“这只是你的工作”。灾难纷至沓来,此后刘星溺水身亡,王丽云、刘耀军一家不仅彻底失去了所有孩子,还彻底失去了生育亲生骨肉的能力。
但李海燕的人物形象在刘星事件之后出现了一个弧度,她反复自责为何事情会这样,为何是自己让王丽云失去生育能力,又为何是自己的儿子害死了他们的独子。这样的自责一直延续,随着王丽云随夫南下而积累熟成,终于成为她一生的遗憾。王丽云最后死于脑部肿瘤,死前她邀请两鬓花白的刘耀军、王丽云回到包头,对王丽云耳语:“我们有钱了,不怕了,可以生了。”到这里才算彻底放下,殊不知在她天人交战的二十年间,王丽云早已放下了,或者如蔡康永先生所言,是“算了”。
何苦何苦,“犹如自造箭,还自伤其身。内箭亦如是,爱箭伤众生。”
2.意象
意象的本意是客观物象经过艺术再创造后被创作主体重新赋予含义的主观形象。如李白笔下的长安、蜀道、明月与他自己。而在电影的语境下意向是一个更暧昧的词,许多电影评论作品会用三五千字就某位导演某部电影的某一个意象反复陈说,论述其背后的心理学与符号学意义。首先不论学界当下越来越多的对电影符号学的斥驳,我个人想要批判的点在于,我们应该更多关注那些给电影赋予“心像“意义的内容,比如视听语言和剧情张力。就我个人的拍摄经验而言,许多可以被”事后诸葛亮“的意向很多时候是在片场被发掘出来的。
对这部电影来说,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意象有4处:筒子楼、医院、货船以及酒瓶。
第一个,筒子楼。这是计划经济时代大概最负盛名的产物,我记得在看《血色浪漫》时,成为大学老师的郑铜和妻子蒋碧云为了得到入住筒子楼的资格不知几番辛苦。而住进了筒子楼,就是有了一个家,虽然这个“家“隔音效果极差,做饭要在楼道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指望不上的。筒子楼压迫了每一个住户的生活空间,强迫他们与自己的左邻右舍社交、互动,也为那个人心最经不起考验的时代造就了许多有真正过命交情的“革命战友”。片中刘耀军、沈英明与高新建三家人便是在这里成为了一生的挚友。沧海桑田之后,三人相继搬离,最后回到这里求个始终的,只有也必须只能是刘耀军夫妇——二十年后,原来因为油烟被熏得发黑发乌的墙壁褪回了灰色,楼梯口那间房成了隐蔽的色情场所,门上挂着粉红的“按摩”霓虹灯招牌。但是自己原来住过的那间同二十年前他们离开时的样子没有任何变化。变与不变何尝不是许多电影的主题,在经历过最不可言说的数十年后,谁变了谁没变,自然会造就富有张力的剧情冲突。
第二个,医院。全片出现了两处我记忆清晰的医院场景,同样的景深全景镜头,同样的平视角度,同样的一道墙分隔开医院的两处空间,一处在第一次出现时是留给抢救刘星的,第二次是留给计生办给王丽云堕胎的;另一处是医院冷静、沉着的医生与护士走下楼梯,头顶是“肃静”二字。这样的对比式拍摄方法任何一个有基本训练的导演都可以想到,但在这部作品的剧情之下,却成为了独创性的试听语言,因为,实在是太惨了。医生的职业性质要求他们保持冷静与沉着,但墙的那一侧,王
丽云面对的是她人生的两次悲剧。这样一对比下来,能承载这种悲伤的景别也只有全景了。
第三个,货船。与其说是货船,不如换之为“工业的回响”。王小帅本人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工业的回响对他而言是长在骨头里的一种表达,一如姜文的电影里总有“北平”的影子。刘星溺水的水库边全是正在行驶的和停泊在岸边的货船,刘耀军和王丽云在福州的居所,每天面对的除了海、沙滩以外,也是货船。这对全片最主要的角色,一生都没有(或者说不愿意,本文作者猜测)脱离那种机械的轰鸣声。影片的最后,他们在福利院收养的“刘星”的替代品,真名为周永福的孩子,带着自己的女朋友,也在那个更靠近赤道,常年与沙滩和海风相伴,永远听得见轰鸣声的“家”里等着他们回去。
最后一个,酒瓶。全片第一次给出刘耀军的形象时,他就在喝酒,小口小口喝着杯子里的白酒。生活可能没有那么如意,但有妻有儿,还有过下去的动力。来到福州后,夫妻二人就是为彼此而活着,这个时候收养的“刘星”也无法为他们带来欢乐,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慰藉。此时的酒虽仍然喝着,用小酒杯盛着,但刘耀军的眼神是空的。“刘星”跟他们闹矛盾决定自己出去讨生活后,刘耀军独自去到海边喝过一次酒,这次他是对瓶吹。喝完后他趔趄着离开,导演留给观众一个大约四秒的小全景,任由上涨的海浪把那个瓶子淹没。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看到这个镜头都会动容,但至少我自己看到这里是感动的。太难了,这么沉痛的悲伤,背在肩膀上真的太难了。刘耀军最后一次喝酒是回到包头带着王
丽云给刘星扫墓。程序走完之后,王丽云从包里拿出一瓶水,自己喝完后递给刘耀军,刘耀军没接,拿起地上刚用来祭拜的酒,对瓶吹。据说这个不接水自己喝酒的动作是王景春自己即兴的,得演员如此夫复何求。
3.时代的宿命与罪过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想要探讨一部跨度为近四十年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去理解背后的时代背景是不妥的。然而,我并没有出生、成长在那个时代,无法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讨论具有浩大宿命感的这四十年的意义,大觉可惜。因此,我只能在我所知道的时代背景下继续阐述我的理解。
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这群人,刘耀军他们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入知青的大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做贡献,从城市走到农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特殊时期国家发展的政策诉求,对于年龄分布从十六到二十四不等的这群青年而言,却是一生的遗憾,落叶归根或客死异乡都是极为常见的归宿。刘耀军、沈英明们无疑是幸运的,他们跟着知青返城大潮回到了城市,一起在工厂里工作,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小家。还没高兴几天,计划生育就来了。关于计划生育,上文已经在剧情意义上提到过不少,这里也不再多进行讨论。不过值得一说的是,王小帅构思拍这部作品的时间,是2015年二胎政策刚刚开放时。
计划生育结束后,王丽云下岗了。工厂宣布她下岗时,镜头从一众前来参加大会的人的全景切给她一个特写,她哭得很伤心。这种群像与个像,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98年,国有单位工作职工8809万人,到2002年时,这个数据断崖式下滑到6924万人。这其中,不知有多少个王丽云——角色的悲剧只是时代造就的更多人悲剧的样本而已。导演用刘耀军的口吻告诉我们,“这是命”。我认识的几位“老三届”对自己前半生的总结,使用最多的判断句也是“这是命”。
时代的宿命与罪过,还有另外一个侧写。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的罗翔教授在厚大法考视频中曾言(B站43275456),1979年刑法中有三大臭名昭著的口袋罪。其中社会生活层面的为“流氓罪”。孙万怀教授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何以成为口袋罪》一文中,为口袋罪下的定义是“口袋罪是对刑法中一些因内容概括、外延模糊而容易混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之罪名的形象称呼。一个罪名之所以成为口袋罪,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条文规定的模糊性,二是司法实践的曲解。”而罗翔教授提到,流氓罪第四款将一切社会生活不轨都定为流氓罪。
流氓罪最高刑是死刑。
1983年陕西日报登载,马某因在家中开舞会且参与者都为男性,被定位流氓罪,事后被枪毙。片中张新建也是因为参加“黑灯舞会”被以流氓罪论处。虽没有严重到死刑,最后也将高美玉娶进了家门,但从影片叙事来看,也被关进去了不短的时间。这是时代的另外一种无奈。
4.死亡与新生
所有的故事都不外乎两个重点——死亡不可避免与生活仍要继续,本片亦然。王丽云被流产时,刘耀军坐的长凳另一侧是一对夫妇,丈夫穿着蓝色的工装,妻子肚子高高隆起,似乎已经足月,这对刘耀军来说恐怕比知道自己的妻子在手术室里更加讽刺。
来到福州后,刘耀军夫妇领养了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刘星”,希望这样他们就能从失孤的情境中得到解脱。但真名“周永福”的孩子永远不能成为刘星,他知道,刘耀军知道,王丽云更知道。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出逃似乎成了必然,周永福离开之后,刘耀军和王丽云二人算是彻底只为彼此活着了。
两人关于生死的态度,或许在沈茉莉事件之后有了一次微妙的转变。王丽云凭借女人的第六感猜到了刘耀军和沈茉莉之间的问题,她没有点破,只是留下一句“耀军,你要是想离婚,我会同意的。”,随后两人就分睡在了两个房间。王丽云自杀的尝试也在这之后,刘耀军抱着王丽云去医院的那个面跟镜头和他抱着当时溺水的刘星去医院的面跟镜头极为类似,甚至互为镜像。当时看到这里的我暗自祈祷,王丽云可千万要被救回来。王丽云被救回来了,此后他二人应该就不怕了,生死无常。
接受李海燕邀请回去包头的飞机上,气流使飞机发生颠簸,刘耀军还紧张了一下。等飞机再度平稳后,王丽云吐槽道:“现在我们怎么还会怕死呢?”
回到包头,成为医生的沈浩有一份体面的医生工作,老婆临产,一切都非常美好。只不过他自己心里有个疙瘩,就是那个当年是自己害死的刘星这件事需要当面对自己的干爸干妈说出来。而实际上,刘耀军和王丽云在出事后不久就知道了,沈英明告诉他们的,他们不希望孩子背负着愧疚过完这一生,他们的宽恕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刘耀军得知沈浩的儿子出生时,自己和王丽云正在墓地给自己的儿子扫墓。这个时候镜头给了一个反拍,全景下带出的是公墓里绵延不绝的墓碑。
影片最后,刘耀军接到周永福的电话,他回来了,还是带着女朋友,浪子回头。但我想,这个时候周永福是否回来的意义都不重要了,回来是锦上添花,不回来,也是没事的。死与新生的轮回,并不受这些事情的影响。
5.生活的重量
《地久天长》故事时间结束的2014年(我推测),我在琴台大剧院看完了赖声川改编的《海鸥》。这部剧最出色的地方是,它没有明确的剧情高潮,把最重要的部分留给了散场音乐里迟迟不肯离去的观众自己体会。《地久天长》给我的感觉非常类似,全片所有的悲伤被表现得相对克制和隐忍,但是作为观众,我却忘不了他们住的筒子楼房间里那种明亮有阳光的质感和船舶、机械、沙滩与海风声构建的热带景象。
生活无法是一次出逃,生活只能是承受。
一位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统计学家,自身处境优裕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走街串巷访贫问哭,绘成一部十七卷本的伦敦贫民图,黑色是不好过,蓝色是忧郁,仿佛在提醒穷人们为什么明明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
而在当下,我们会因为很多事情过得不开心。没人会提醒我们为什么不开心,我们也不会愿意去想。面对不开心,我更愿意报之以简单的四个字:
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