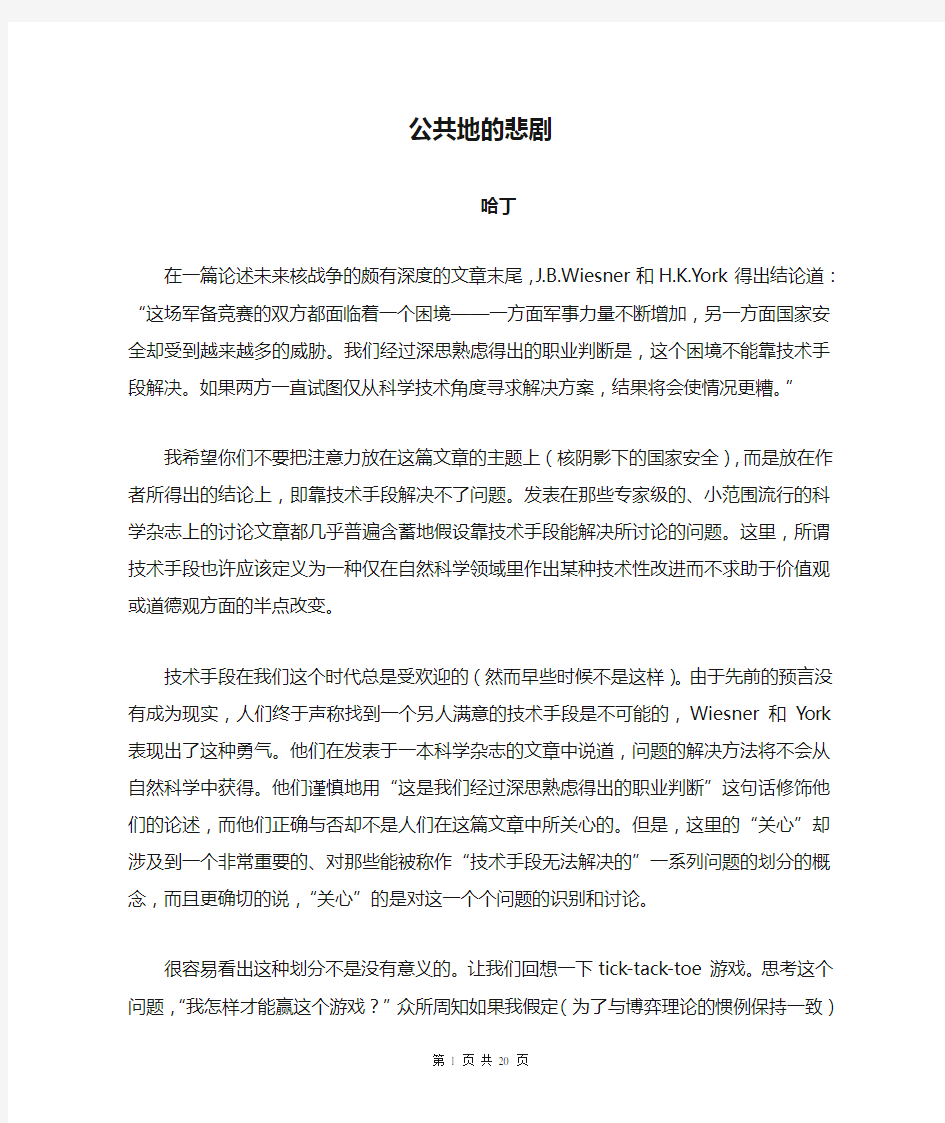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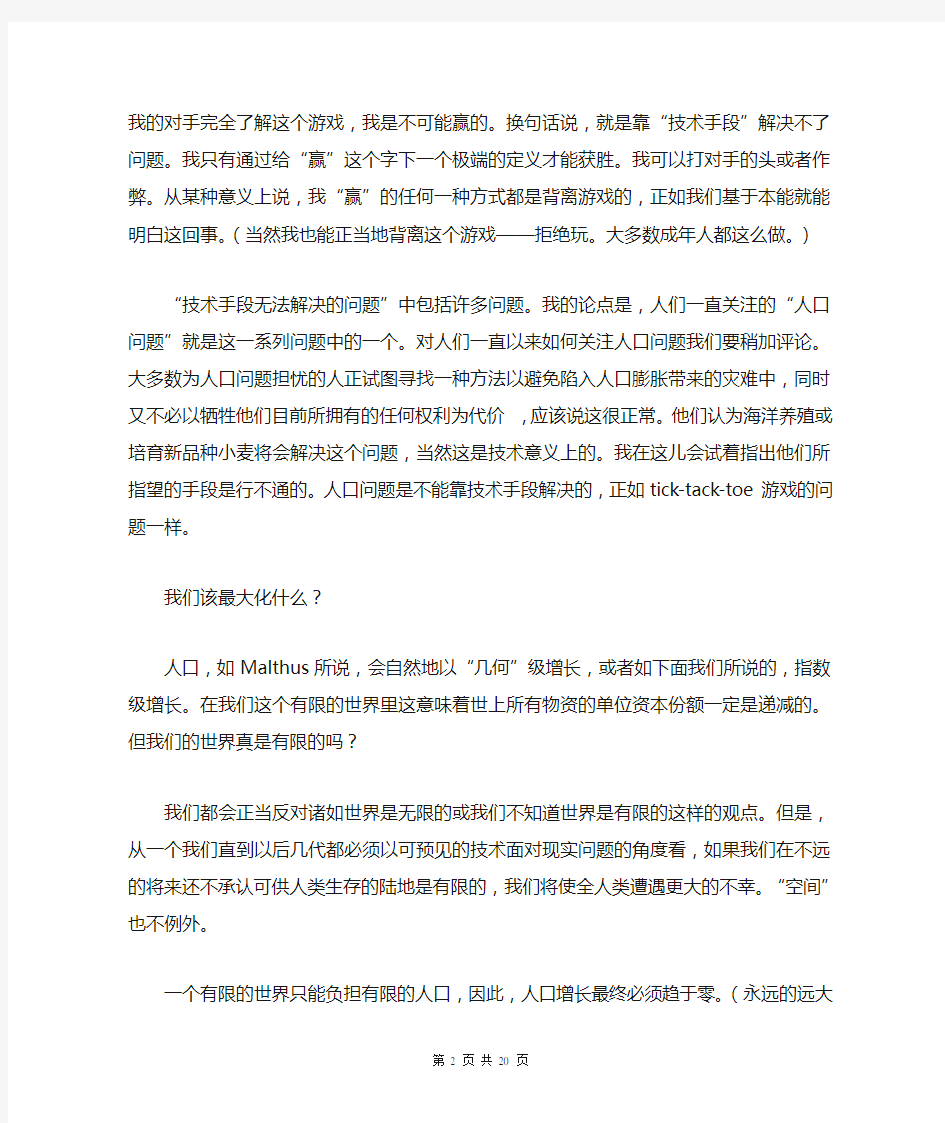
公共地的悲剧
哈丁
在一篇论述未来核战争的颇有深度的文章末尾,J.B.Wiesner和H.K.York得出结论道:“这场军备竞赛的双方都面临着一个困境——一方面军事力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国家安全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职业判断是,这个困境不能靠技术手段解决。如果两方一直试图仅从科学技术角度寻求解决方案,结果将会使情况更糟。”
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这篇文章的主题上(核阴影下的国家安全),而是放在作者所得出的结论上,即靠技术手段解决不了问题。发表在那些专家级的、小范围流行的科学杂志上的讨论文章都几乎普遍含蓄地假设靠技术手段能解决所讨论的问题。这里,所谓技术手段也许应该定义为一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作出某种技术性改进而不求助于价值观或道德观方面的半点改变。
技术手段在我们这个时代总是受欢迎的(然而早些时候不是这样)。由于先前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人们终于声称找到一个另人满意的技术手段是不可能的,Wiesner和York表现出了这种勇气。他们在发表于一本科学杂志的文章中说道,问题的解决方法将不会从自然科学中获得。他们谨慎地用“这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职业判断”这句话修饰他们的论述,而他们正确与否却不是人们在这篇文章中所关心的。但是,这里的“关心”却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对那些能被称作“技术手段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的划分的概念,而且更确切的说,“关心”的是对这一个个问题的识别和讨论。
很容易看出这种划分不是没有意义的。让我们回想一下tick-tack-toe游戏。思考这个问题,“我怎样才能赢这个游戏?”众所周知如果我假定(为了与博弈理论的惯例保持一致)我的对手完全了解这个游戏,我是不可能赢的。换句话说,就是靠“技术手段”解决不了问题。我只有通过给“赢”这个字下一个极端的定义才能获胜。我可以打对手的头或者作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赢”的任何一种方式都是背离游戏的,正如我们基于本能就能明白这回事。(当然我也能正当地背离这个游戏——拒绝玩。大多数成年人都这么做。)“技术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包括许多问题。我的论点是,人们一直关注的“人口问题”就是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对人们一直以来如何关注人口问题我们要稍加评论。大多数为人口问题担忧的人正试图寻找一种方法以避免陷入人口膨胀带来的灾难中,同时又不必以牺牲他们目前所拥有的任何权利为代价,应该说这很正常。他们认为海洋养殖或培育新品种小麦将会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是技术意义上的。我在这儿会试着指出他们所指望的手段是行不通的。人口问题是不能靠技术手段解决的,正如tick-tack-toe游戏的问题一样。
我们该最大化什么?
人口,如Malthus所说,会自然地以“几何”级增长,或者如下面我们所说的,指数级增长。在我们这个有限的世界里这意味着世上所有物资的单位资本份额一定是递减的。但我们的世界真是有限的吗?
我们都会正当反对诸如世界是无限的或我们不知道世界是有限的这样的观点。但是,从一个我们直到以后几代都必须以可预见的技术面对现实问题的角度看,如果我们在不远的将来还不承认可供人类生存的陆地是有限的,我们将使全人类遭遇更大的不幸。“空间”也不例外。
一个有限的世界只能负担有限的人口,因此,人口增长最终必须趋于零。(永远的远大于或小于零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变体,不需要讨论。)当出现这种情况,人类将面临着什么?特别地,Bentham的“最大数量的最大利益”的目标能实现吗?
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有两个,而任何一个都能给出满意的解释。理由一是从理论方面入手的,因为数学上不能同时最大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对此von Neumann和Morgenstem 有清楚的论述,但这条原则隐含在不完全微分方程理论中,至少可追溯到D’Alembert (1717-1783)。
理由二是直接来自于生物学事实。为了生存,任何生物体必须拥有能量来源(如食物)。这些能量用来满足两个目的:维持生存和工作。一个人维持生存每天大约需要1600.000卡路里(“生存热量”)。而他所做的任何尽用以维持生存的举动都被定义为工作,它们是要靠他所吸收的“工作热量”维持的。工作热量不仅用以维持我们日常所指的工作,它们也维持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从游泳、赛车到音乐演奏和写诗。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使人口数量最大化,什么是我们必须做的就很清楚了:我们必须要使每个人的工作热量尽可能地趋近于零。没有美食、没有假期、没有运动、没有音乐、没有文学和艺术……我想每个人都会绝对地同意人口数量的最大化并不是财物的最大化。Bentham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得出结论之际,我已作出平常的假定即问题就出在能量的获取上。原子能的出现已经或多或少导致对这一假定的质疑。然而,即使能量是无穷尽的,人口增长仍会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能量的获取问题被其耗费问题所取代,J.H.Fremlin对此做出了充满智慧的论述。在分析中算术记号可以说被颠倒了过来,但Bentham的目标还是无法达到的。
所以,最佳的人口数量是小于最大量。但如何定义这最佳量恐怕又要大伤脑筋,据我所知,还没有人认真地对待过这个问题。要找到一个稳定而又另人信服的解决办法显然是要几代人做出艰苦的分析工作和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得到最大的利益,但利益是什么?对于某人来说利益是一方荒野,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又是一座能容纳几千人的滑雪旅馆。利益对于这个人意味着能拥有海湾以放养鸭子满足狩猎者的要求,而对另一个人则意味着能占有一块工地。我们常常说不能在利益之间作比较,因为利益是无法衡量的。而无法衡量的东西是不能比较的。
理论上这也许正确,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衡量的东西却可以衡量,只不过需要一套评价准则和一个衡量系统。大自然保留了这套评价准则。物种是体形小而易于躲藏好,还是体形庞大而充满力量好?这种“无法衡量”却是通过自然选择得以被衡量的。而最终取得的折中办法是依赖于自然对各种变量价值所采取的评价。
人类必须模仿这个过程。毫无疑问,事实上人类已经在这样做了,只不过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而正是隐藏在背后的决定被明晰的那一刻,讨论开始了。接下去几年所要面对的问题是提出一套让人接受的衡量理论。相关的辅助性效果、非线形变化和对未来的折现的困难使得这个智力问题颇难对付,但在原理上是可以解决的。
是否有任何文化团体解决了目前这个现实问题,哪怕是直觉上感到可以解决的?一个简单的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团体成功过:当今世界还没有、哪怕有过一段时期保持零增长率而繁荣的人口。任何已经本能地确定人口最佳点的人将很快发现这个事实,在达到这个最佳点之后人口增长率为零并保持下去。
当然,人口的正增长率也许可以证明该人口还未达到最佳点。但是以任何合理的评价标准来看,现在这个地球上增长最快的人口(一般来说)是最不幸的。这种关联(它并不需要一成不变)使得人们质疑人口的正增长率是说明人口还未达到最佳点的证明这一乐观假定。
如果我们不明确地驱散亚当.·斯密在实证人口统计学领域的巨大影响,我们就不会在最佳人口规模的研究上取得成就。在经济事务方面,《国富论》(1776)使“看不见的手”闻名遐迩,指出一个人“只从他自己利益出发”却能被“看不见的手”引领着促进公共利益。亚当·斯密并没有断言这永远正确,也许他的追随者也不这么认为。但是他却促成了一直以来妨碍基于理性分析的积极行动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趋势,它假定每个单独的人的决定实际上对整个社会应该也是最好的。如果这个假定成立,它就证明我们现行的对再生产的不干
涉政策应该保持下去,我们也能假设人们能控制他们的生殖欲以便达到最佳人口数量。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我们就需要重新考虑个人自由以便发现其中哪些是需要保护的。
公地自由的悲剧
对于那只看不见的手对人口进行控制的反驳可以在一位叫Willian Forster Lloyd(1794-1852)的业余数学家在他1833年的一本小有名气的小册子第一次所收录的电影剧本中找到。我们还是称其为“公地的悲剧”较好,象哲学家Whitehead一样使用“悲剧”这个词:“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悲剧本质上并不是不幸的,它存在于事物无情作用的庄严肃穆中。”他又继续说道,“只有从人类生命中那实际上包含着不幸的各个片段的角度,才能说明这种无法逃避的命运。因为只有这些片段才能在戏剧中表现出逃避是没有用的。”
公地的悲剧以这种方式发展着。让我们想象一块对所有人都开放的草地。在这块公共地上每一个牧人都会尽可能多地放牧他的牲畜。这样一种模式也许会另人满意地持续几个世纪,因为部落争斗、偷猎和疾病一直使得人口及牲畜数量都大大低于土地的承受限度。但随后人类学会了计算,也就是说,一个可以长期追求社会稳定这一目标的时代来临了。此时,对公共地的出于本能的逻辑思维就会产生无情的悲剧。
作为理性人,每一个牧人都期望他的收益最大化。不管直白还是隐晦,或多或少地他都会问,“给我的兽群多增加一头牲畜,对我来说有什么效用?”这个效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影响。
1.正面的影响是使牧群总量增加了。因为这个牧人能通过变卖这头额外的牲畜得到全部的收益,所以效用几乎能达到+1。
2.负面的影响是由这额外的一头牲畜所引起的过度放牧。因为不管怎样,过度放牧是由所有的牧人承担的,对于**(原文中是乱码故无法翻译)牧人的任何特定的决定,其负面效用只是-1的一部分。
将所有的影响加总,理性的牧人会得出结论:对于他来说,使他的牧群多增加一头牲畜是个明智的选择。但是其他每一个共用这块草地的理性的牧人也会得出如此结论。所以悲剧就发生了。每一个人都陷入到一个促使他无限制地增加牲畜数量的机制当中,而他们所处的世界是有限的。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的社会里,每一个追逐个人利益的人的行为最终会使全体走向毁灭。公地自由会毁掉一切。
有些人会说这是陈词滥调。但真要是这样就好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几千年前人们就已经了解其中奥妙,但自然选择认同心灵的自制力。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他是依靠他拒绝承认以下事实的能力而获益的,那就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可以牺牲整个社会的利益,尽管他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教育可以防止人依本能做错事,但残酷的生命繁衍却要求作为根基的知识系统不断更新。
几年前在Leminster发生的一件小事——Massachusetts指出了知识有多么僵固。在圣诞节购物旺季,商业区的停车计时器充斥着贴着“不要在圣诞节前打开市政部门提供的免费停车场”标签的塑料袋。也就是说,市领导们面对一个空间已经缺乏但需求仍不断增加的前景,重新建立起公共系统。(讽刺的是,我们却怀疑这些领导凭借这个倒退性的法案获得了更多的选票。)
类似的,公共地逻辑也许早在农业的诞生或者是私人产权的发明时就早已为人们所了解。但是它大多却只是在那些没有被有效归纳的特殊情况下被人们所了解的。甚至在最近,那些在西部山区租用国家土地的牧人对此的理解仍只是处在矛盾中,他们仍然不停地向政府施压,要求增加放牧的牲畜数量直到因过度放牧引起土壤侵蚀和杂草从生。同样的,全球海洋也因为公共地哲学而不断受到威胁。沿海国家仍然主动地响应着“公共海洋”这一号召,他们一边嘴上声称自己坚信“海洋资源取之不尽”,一边让鱼类和鲸类一个接一个地濒临灭亡。
在解决公共地悲剧方面国家公园是另一个例子。目前,它们毫无保留地对全体开放。公园本身是有限的——只有一个Yosemite Valley——但是人数似乎是无限制地增加,公园的价值对游客来说就是逐渐减少的。坦白说,我们必须立即停止将公园当作公共地对待,否则它们对于任何人将毫无价值可言。
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有几个选择。我们可以把公园变卖使之成为私人财产,我们也可以继续把它们当作公有财产但分配进入公园的权力。分配的依据也许是基于人们的富裕程度,这可以通过一个拍卖机制实现。也可以依据人的才能,只要得以受到一些大家公认标准的约束作为保障。也可以考虑通过中彩票的方式,或者根据先入为主的原则,采用排队的方式解决。我想,以上这些都会受到人们的反对。但我们必须从中选择,要么放任我们称之为公共地的国家公园不断遭受破坏。
污染
公共地悲剧在污染问题中是以一种相反的方式重新出现的。在这里不是一个从公共地获取的问题,而是诸如把下水道污物、化学物质、放射性污染物和高温废弃物等物质排放到水体中、将有毒废气排放到大气中,以及眩目的广告引起使人体不适等问题。效用的计算方法与前面一样。理性的人会发现他向公共地排放垃圾后,自己所承担的成本要小于排放垃圾前为它们作净化处理所承担的成本。因为这在每一个人看来都是正确的,所以只要我们像独立、理性而自由的企业家那样行事,我们就会陷入到一个“污染自家”的怪圈。
通过私人产权,或者类似的形式可以避免象食品篮子似的公共地悲剧。但我们周围的空气和水源却无法通过这种形式得到保护,所以必须靠另外的方法避免另一种如同污水池的公共地悲剧,比如可以通过强制的法律手段或税收机制使排污者自己处理垃圾的成本小于不作任何处理就丢弃垃圾的成本。对于这两种悲剧我们都还未取得任何进展。实际上,我们所指的私人财产这一概念(尽管可以防止我们耗尽地球的所有可利用资源)是赞同污染的。一个拥有一座位于河堤的工厂的人(他的私有产权范围一直延伸至河的中部)会经常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权力使流过他门口的河流变得浑浊。法律,尽管总是后生的,要求不断的补充和改进以使它适应这种新发现的公共地。
污染问题是由人口问题引起的。它并不关心一个孤独的美国边境居民如何丢弃垃圾。“河流每隔10英里就会自己净化一次,”我的祖父过去常常这样说,并且在他孩提时,差不多这个故事就是真的,因为那时居住的人并不多。但随着人口的增长,自然化学物和微生物循环不堪重负,就需要对产权的重新界定。
怎样制定自律法?
对由人口问题而引发污染问题的分析,使得我们发现了一条并未被广泛认识到的道德准则:某一行为在其被实施的那一刻,它的道德价值是此时整个系统所处状况的一个函数。把公共地当作污水池并不会不利于生活在边境的普通民众,因为那儿更本就没有民众;而相同的行为若发生在大都市,恐怕就不能让人忍受了。150年前,一位平原居民会宰杀一头美洲野牛,割下它的舌头当作晚餐而丢弃剩余部分。我们并不能严格地认为他这样做是浪费的。今天,由于全世界只有几千只野牛得以幸存,我们会惊骇于以前这种杀戮野牛的行为。
过去,靠照片判断某一行为的道德价值会受益匪浅。人们只有了解了一个人行为发生时的全部背景,才能知道他宰杀一头大象或者烧掉一块草地会不会伤害到别人。“一张照片抵得一千句话,”一位年迈的中国智者这样说;但是这也许要用一万句话来证明其正确性。这对于生态学家就像对一般的改革家试图通过照片这一捷径去说服别人一样诱人。但是一场争论本质上是不可能通过照片得以表现的:它必须以理智的形式——语言来表现。
过去大多数整理道德伦理学说的人都忽略了道德对制度是敏感的。“汝不应当……”是不以特定情况评价道德的传统指令。我们社会的法律遵循古代伦理学的样式,因此不太适合统治一个复杂、拥挤和多变的世界。我们周而复始地将行政性法律补充进成文法。因为具体
操作中不可能把保证你在后院安全地焚烧垃圾或者是安全地驾驶一辆汽车的所有情况都一一列举出来,所以靠法律的授权,我们得以把细节反馈到政府机关,结果就成了行政性法律。但最近这种行政性法律受到了人们的正当忧虑:谁来监督执法者?John Adams说我们必须成立一个“不是由人而是由法律控制的政府。”行政机关的那些试着在整个制度体系下对行为进行道德评判的管理者在离开监督时总有腐败的倾向,结果造成一个由人而非法律控制的政府。
禁令是容易制定的(尽管没有强制执行的必要);但是自律又如何制定?经验告诉我们,可以通过行政性法律的仲裁达到这一目的。如果我们假定Quis custodiet这种情感阻止我们使用行政性法律,我们就能对不必要的可能性做出限制。最好把这句话牢牢记住,永远把它当作一个我们无法逃离的危险那样以作警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挑战是能否想出一种中和的反馈以保证监督者诚实可信。我们必须想出如何使监督者及中和了的反馈都得到合法的权威性。
不能容忍无节制生育
在人口问题上,公共地悲剧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一个仅有“丛林法则”统治的世界中——假如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家庭所拥有的孩子数量决不会造成公众难题。过度生育的父母将有较少的后代而不是更多,因为他们无法同样地照顾每一个孩子。David Lack和其他人已经研究得出,这种消极的反馈明显地控制着鸟类的繁衍。但人不是鸟,至少已经几千年不象它们那样生活了。
如果每个家庭只完全依赖它自己的全部资源;如果不懂得节省的家庭使得孩子因饥饿而死;如果这样,过度生育就会“惩罚”自己,进而控制生育。接着就用不着公众来关心家庭的生育问题了。但我们的国家已深深地受制于福利状况,因此又面对公共地悲剧的另一面。
在一个福利国家,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像家庭、信仰、种族抑或阶级(或者实际上任何有别于其他的团体)这样容许超生以保证其本身的不断壮大的情况?将自由地生育这一概念扩展并且相信每一个出生的人都享有使用公共地的权力,会使这变成一个悲惨世界。
不幸的是,这恰恰是美国正努力说服大家所做的。最近在1967年,30个国家达成以下共识:“《人权宣言》将家庭描述成社会的自然的基本单位。任何有关家庭规模的意见和建议必须最终取决于家庭自己,并且任何人无权代为定夺。”
对于不得不明确拒绝承认这个权利的合法性,我们深感无奈;否定它,让人觉得像一个Salem的居民——Massachusetts在17世纪否认女巫的存在一样不自在。现在,在自由主义阵营中,某种像禁忌的东西在抑制对美国的批评。有一种美国是“我们的最后也是最好的”情感,“我们不应该挑它的刺,我们不应该为原始的保守而奋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Robert Louis Stevenson所说的话:“朋友间的真理总是敌人最易上手的武器。”如果我们坚信这条真理,我们就必须公开否定《人权宣言》的正确性,尽管它是由美国促成的。我们还应该赞同Kingsley Davis为使拥护家庭团体式管理的人看到在追求相同悲剧性理想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而作的努力。
良心使人自我净化
如果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可以通过求助良心来控制人类的繁衍,那这将是个错误。Charles Galton Darwin在纪念他祖父的著作问世100周年时提出了这一说法。这个论点坦率而又有达尔文主义。
人是多样化的。面对控制生育的呼声,毫无疑问有的人会比其他人更积极地回应。而那些有更多孩子的人则会使他们在下一代中的比例较之那些有着更敏感良心的人大得多,并且这种差距会随着一代又一代得到强化。
用C.G .Darwin的话来说:“也许生殖本能要花费数百代人的时间以这样的方式演进,但是如果这是必须的话,自然早就进行报复了,而且Homo contracipiens(该词查不到)的多样
性就应该消失并为Homo progenitivus的多样性所取代。”
这个论点假定良心或者要孩子的欲望(不分男女)是遗传的(这里的遗传仅指最通常正式的意义)。无论这种看法是源自生殖细胞还是如A.J.Lotka所说的是“不言自明的”,结果都一样。(如果人们两者的可能性都否定,我们的教育有何意义?)我们这儿是在人口问题的背景下提出这个论点的,但它同样也适用于任何其他事例,如社会通过让人良心发现来呼吁利用公共地资源的人为了集体的利益而限制自己的行为。做出这样的呼吁也意味着建立起一套机制,用以消除竞赛中出现的良心。
良心的原发性作用
虽然长期呼吁人们良心发现的不利影响是会招人谴责的;但这样做同样有着短期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以“良心的名义”劝说一个正利用着公共地资源的人停止行动,我们会说什么?他会听到什么?不仅当时,而且在他晚上半睡半醒时的哪怕极短暂的一刻,他不但会想起我们所使用过的词语,还有我们无意识中暗示给他的非语言信息。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迟早会感觉到他有过两次交流,并且它们是互相冲突的:1.(有意的交流)“如果你不安我们说的去做,我们会公开谴责你没有按照一个令人尊敬的公民所应该做的那样表现”;2.(言外之意的交流)“如果你听从我们的建议,我们只会暗地里指责你这个笨人,让你羞愧地站在一边看着除你之外的人利用公共地的资源。”
所以每个人就都受到Bateson所说的“双重束缚”。Bateson和他的同事已经似乎合理地解释了“双重束缚”是引发精神分裂症的一个重要因素。“双重束缚”并不总是具有破坏性的,它只经常使得受它作用的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出现危机。“不好的良心就是疾病。”Nietzsche 说道。
对于那些希望自己能超出法律的限制去控制他人的人来说,能够对别人的良心施法术总是个诱人的想法,位于最上层的统治者也不例外。历史上有哪一位统治者不是成功地号召起劳动者联盟让他们自己为了更多的工资而节制其需求,或者使企业团结起来以能自愿地指导价格为荣?我不记得有过这样的情况。在这种场合下所使用的修辞是使那些非合作者感到罪恶感。
几个世纪以来,似乎内疚都是文明的一个有价值的、或许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这一点不需要证明。今天,在这个后弗洛伊德的世界,我们却怀疑这一点。
Paul Goodman 以现代的观点讲道:“利益从不来自于内疚感,也不出自于智力、政策或同情。内疚的人并不理会目的如何,而只关注他们本身,而且甚至有意义的是,内疚的人关注他们的焦虑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一个人不必是职业的精神病学家就能了解焦虑的后果。我们西方世界刚刚从长达两个世纪噩梦般的性黑暗时代(Dark Ages of Eros)解脱出来,那个时代是依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法律、但也可能更有效地通过产生焦虑的教育机制来维持着的。对此,Alex Comfort 早已在《焦虑的产生》一书中详尽地论述过;但讲得并不漂亮。
因为很难证明,所以我们便可以甚至承认,从某些角度看,焦虑的结果有时是可取的。我们进一步问的问题是,因为政策这个理由,我们是否应该鼓励使用会使人心理倾向于(如果不是故意的话)发病的技术手段?近来我们听到许多关于称职父母的讨论;这两个相关联的词也被添加进授予那些对计划生育有突出贡献的组织的头衔中。一些人已经建议发起一场全国范围的(或全世界的)、向父母们灌输生育责任的宣传运动。但什么是良心这个词的含义?当我们在维护道德的重要约束力缺失时使用“责任”这个词,我们是不是正试图威逼一个自由享有公共地资源的人去做有损他利益的事?责任是个为了物质利益而伪造的说法,它试图不劳而获。
如果责任这个词一定要用,我建议取Charles Frankel给它所下的定义。“责任,”这位哲学家说道,“是明确的社会分工的产物。”注意,Frankel号召的是社会分工而不是宣传。
达成共识的相互制约
产生责任的社会分工也是产生某种制约的分工。想想抢劫银行,那些从银行抢钱的人多把银行当作公共地。我们怎么阻止这样的事发生?当然不是通过仅仅靠嘴上呼吁他们要有责任感来限制其行为,与其这样,还不如以Frankel为榜样靠宣传强调银行不是公共地;我们尝试明确的社会分工以阻止银行变成公共地。这样虽然侵犯了潜在抢劫者的自由,但我们既不否定也不后悔。
抢劫银行的道德特别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完全同意禁止这种行为。我们愿意说“汝不应抢银行”而不接受任何借口,但制约也能产生自律。税收是一个不错的制约机制。为了使商业区的顾客适度使用停车场,我们引进了供短时间停车的投币式计时器,以及对长时间地停车进行罚款。只要一个人愿意,我们实际上不需要禁止他停车;我们只要使其停车越久,所付的钱越多即可。我们提供的不是禁令而是一些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自由选择。一个美国广告人也许会称其为“说服”;而我更偏爱制约这个词的坦率。
制约在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眼里现已成为一个肮脏的词,但是这不会永远这样。通过理直气壮地重复使用这个词,我们会接受它,正如****(原文是its dirtiness can be cleansed away by exposure to the light)这个成语所说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制约这个词暗示着幕后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僚们的专横决定;但这样想多虑了。我所指的制约是相互性的,已由所有牵涉到的人达成了共识。
说我们彼此同意相互制约并不是说我们也要对此欣然接受,或甚至装作我们乐意接受。谁会乐意被征税?我们私下里都不断抱怨。但我们都同意强制性征税,因为我们意识到自愿缴税只会便宜了那些没有羞耻心的人。我们建立和支持(尽管私底下会抱怨)税收制度和其他的制约机制以摆脱以公共地为荣的心态。
用来替换公共地的方案不必最好只要更佳即可。在财产地位和其他物质的保证下,我们所做出的选择是将社会事业机构私有化及承认其继承的合法性。这个体系是否完全公正?作为一个受过遗传学方面训练的生物学家,我否定它是。对于我来说,如果个人在遗传方面存在差异,那财产的合法拥有就应该完全与生物遗传相匹配——那些在遗传意义上更有能力也更适合管理财产的应该合法地继承更多的财产。但是遗传学工程总是使我们的继承法中对“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一教条的拙劣仿效变得晦涩含蓄。一个白痴可以继承数百万财产,而且信用基金可以使他的钱免遭掠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私人产权包括继承这一体制是不公正的,但我们不得不将就,因为我们现在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发明一个更好的体制。公共地的替代物是什么?这个问题令人颇感惊骇,以至于不能想到答案。不公正总比完全毁灭要好。
介于改革和现状间的福利总是为双重标准随意地左右,而这是它众多特点中的一个。无论何时提出一项改革措施,它都会因为它的反对者得意地指出它的哪怕一个小极的疏漏而流产。正如Kingsley Davis所指出的,坚决拥护现状的人常常暗示,没有全体人都同意,任何改革都是行不通的,而这种暗示与历史事实是不符的。我几乎可以说,对所提出改革措施的自发反对是基于以下两个没有意识到的假设中的任何一个:(1)假设现状是完美的;或(2)假设我们所要作出的选择不是改革就是什么都不改,非此即彼;若改革措施是有疏漏的,根据假设我们就应该什么都不做,而是等着一个完美的措施诞生。
但是我们不能无所事事。我们数千年来一直坚持的就是行动。行动也产生罪恶。一旦我们意识到维持现状意味着行动,我们就能将目前已了解的优势劣势和所提出的改革措施的优劣势作一比较,以尽可能地克服我们经验不足的不利条件。在这比较的基础上,我们就能作出理性的决定而摈弃那些只有完美的体制才能允许的难以实行的设想。
对必需品的认可
也许对人口问题所做的最简单的概括是:公共地如果对所有人完全公正,就必须以低密度人口为条件。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公共地的公正也会在这或那方面难以维持。
首先我们会在收集食物方面将农地围以篱笆,限制草坪、鱼塘的使用及在这些地方进行狩猎活动。不过这些限制在全世界范围都不是绝对的。
接下去不久我们也会看到,把公共地当作垃圾场也行不通。西方人普遍遵守对于家庭下水道污物排放的限制;我们仍正努力地阻止由汽车、工厂、农药喷洒及施肥和原子能装置向公共地排污。
我们对于公共地悲剧的认识还停留在一种非常幼稚而愉快的程度上。对于公共媒体电波的传播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消费者一直受到杂乱无章的音乐的攻击而没有事先征得他们的同意。我们的政府已在制作一种为满足任何一个人能早3小时从此海岸到达彼海岸而骚扰50,000人的超音速客机上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无数的广告不仅污染了穿行于空中的广播、电视信号,并且还污染了游客们的视野。为了自己的愉悦而非法地利用公共地,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这是不是因为清教徒的遗传使我们把愉悦视为罪恶而把痛苦(即广告污染)视为美德?
对公共地使用的每一种限制都意味着有的人的个人自由受到侵害。以前,这种侵害能为人所接受,因为同时代的人并没有抱怨他受到的损失。而新近这种形式的侵害我们是要激烈反对的,“权力”和“自由”的呼声不绝于耳。但自由是什么?当人们达成共识一致通过禁止抢劫的法律时,人们得到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更少。禁锢于共享公共地这一逻辑的人只会好无约束地走向灭亡;一旦他们意识到互动制约的益处,他们就会主动帮助实现他人的目标。我记得是Hegel说的,“自由就是对必要性的认可。”
我们现在所必须认识到必要性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节育的必要性。技术手段决不能把我们带离人口过度带来的灾难。自由生育会毁了一切。此时,为了避免困难地下决心,我们会对良心和父母责任感大肆宣传。这种倾向必须被制止,因为单独对起代理作用的良心的大肆宣传会导致将来的所有良心都消失,而在短期,焦虑会大大增加。
我们可以保留的、支持其他和更值得珍惜的自由的唯一做法是放弃自由生育,并且这会很快实现。“自由就是对必要性的认可。”并且这也是教育在呼吁所有节育必要性方面的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结束这个意义上的公共地悲剧。
参考文献(略)
其他有关文献
再论公共地悲剧
Beryl Crowe(1969)
再版于《公共地管理》哈丁、John Baden W.H. Freeman, 1977; ISBN 0-7167-0476-5 “在现代自然科学领域已经形成一种认识,那就是例如人口问题、核战争及环境污染等问题都有一个子集。而这些是无法靠技术手段解决的。
同样,还有另外一种认识正得到越来越多现代自然科学家们的认同:人口、核战争、环境污染和城市生态环境的恢复等问题都有一个子集,对于这些目前的政治手段无能为力。这篇论文的主旨是,这两个子集所分担的公共区域包含了大部分对现代人来说生死攸关的关键问题。”
对避免悲剧的一些设想
“为了放弃靠技术手段解决转而求助于政治和社会领域,哈丁给出了以下三个重要设想:(1)存在或者可以建立一套批判标准和衡量系统,以将生活中那些不可衡量的转变成可衡量的;
(2)牢记‘制约可以相互认同’这一评价准则并正确应用,对于在当今社会中影响一个问题解决方案的诞生是很有效的;
(3)由上面的评价准则及普遍的制约所支持的管理系统将能够阻止公共地被进一步破坏。”
不断消逝的公共评价系统神话
“在美国,直到最近还存在着一系列也许能使哈丁所指的子集的解决成为可能的条件;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民族……’的神话中,这种幻想主张我们的国家是整个世界的熔炉,而在这多元化社会中,欧洲这粒矿石被投进国家间的交流这一坩埚中以生产新的合金——一种美国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应该是由一个公共评价系统联合起来的,该系统民主、公正,并且存在于宪法及《权利法案》包含的普适的强制性规则中。
但是今天的美国正显露出一系列新的行为模式,这说明那个神话将要或者已经完结了。大部分人已不再相信这个神话,也不再照它行动,而是发展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尊重社会等级制度。这种制度使得现在的美国人较之他们以前自己形容他们的文明如同光亮的合金,更像是一个地缘接近的‘部落’组织那与众不同的、原始的形式。”
“看看最近对核心城市病态的分析,Wallace F. Smith指出经济学分析已不再适用于城市产出模型,他进而提出的模型是将城市视作一个享受闲暇的地方,这似乎就意味着这个模型的本质是城市是不可能重新恢复健康的,因为闲暇需求是以价值为基础的,所以没有折中及和解;因此对于目前这些核心城市中以价值为导向的需求没有决定的方法。
在寻找公共评价系统这一神话不断弱化的原因时,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对其他团体的感觉和认识主要是来自于以笔为媒介的交流形式,美国是由平等主义者组成的一个巨大的熔炉这一幻想就会停止。也许不明显,但在知觉方面人是受利益驱动的。利益总是能通过牺牲价值得到调和并使健康免遭破坏。但是受电子媒体的影响,心理距离不断缩短,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我们可以与之在利益上调和的人竟然不是受利益驱动而是价值。他们在我们的卧室里所表现出的行为显示出一系列有别于我们的价值观,因此我们作出的让步并不是契约性的而是文化性的。当接受前者时,任何文化性让步的形式都不是理性行为的表现,而是异教徒似的状况。因此,我们已进入到一个包容而不是冲突的时代,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衡量的’仍是‘不可衡量的’。”
强制垄断神话的消逝
“过去,那些再也不受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限制的人总是受‘政府在强制力上居垄断地位’这一神话左右。自从二战以来,由于流动性福利政策的成功,这个说法的神话色彩一直在减弱。这种政策首先推行于法国的Indochina,之后自然地在Algeria得到推行。我们受参议员Fulbfight所说的‘权利的傲慢’的苦,我们太久才吸取在Vietnam的教训,尽管我们现在意识到战争的本质是政治而不可能靠军事解决。很明显,强制垄断的神话不断失去支持者,最初它在南方公民权的斗争中得到名分,然后是在我们城市中的黑人居住区,接着是在芝加哥的马路上,而现在却在我们学校里。流动性福利技术使以下事实变得明明白白:尽管国家能打胜仗,但它却无法在价值观的战争中获胜。除非国家愿意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以排除那些有异议的团体,否则现代国家面对占总人口10%的积极反对的人,它们拥护的强制力不会维持多久。过去维持暴力神话的原因是人们接受公共评价系统,但它存在与否现在却受到怀疑。”
公共地管理者神话的消逝
“实际上,这种方式已得到普遍推荐,它可以使一位作家为了尝试发展所有规范性政策而要求公共的生命周期。这种周期由如此多顽强的反对声实现,这些声音产生了足够大的政治影响力以成立一个规范机构来保证所有人都能公平、公正和理性地享有公共地的好处。这样当这个机构投入运行时,会出现一种局面,就是会在大部分享有一般的但不是制度化的公共地利益的人中形成一段时期的政治沉寂,接着那些被触怒的人会象征性地出现焦虑。一旦这种政治沉寂持续一段时间,那些希望侵犯公共地的高度组织化、分工明确的利益团体就会顶住足够的压力,通过其他政治途径使机构转变为保护和扩展它们的利益。在这种局面下,甚至规范性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来自于不同等级中的机构管理者。”
公地悲剧的终结者:广场舞大妈 ——两城环境卫生改进的建议人不臆想无少年,今日我臆想的题目是城中村环境、城乡结合部环境(简称两城环境)与城市社区的环境卫生差异原因。看着挺好的出发点,为什么是臆想的那?现在给出解释,两城环境卫生不一定糟糕,城市社区的环境不一定美观,简单说它们之间的差异极有可能是我自身的杜撰。 要论两城环境和社区环境的差异原因,除了经济条件差、外来人口居多等因素外,还有一个差异就是是否有广场,广场上是否有经常活动的大妈。要解释为什么大妈也会成为影响因素之一,更准确说是广场舞大妈,没了它们,广场极有可能成为垃圾的堆放场所。为了进一步解释,这里选用公地悲剧进行辅助。 1、什么是公地悲剧; 2、两城环境与城市社区环境差异存在的原因; 3、糟糕的两城环境卫生可以类比为公地悲剧的原因; 4、两城环境卫生的终结者——广场舞大妈的原因。 一、公地悲剧 据百度百科释义:公地悲剧,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而每一个人都倾向于过度使用,从而造成资源的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公地悲剧的解决原因有二:其一,公地变私地,即产权私有化,也是最受推崇的公地解决办法。产权私有化有利有弊,利处是它确实可以杜绝公地悲剧的发生,局限是该产权可以私有化和私有化对拥有人有静利润,另外还会造成财富向一端聚集;其二,加强管理,即通过规则的制定确定谁有优先使用权,在不阳光的情况下,该办法极易发生寻租行为。 不过这里有一个疑问,公地一定要悲剧吗?自然不是,比如沙漠、风等资源,储量太大、用途有限,让他们悲剧很难;又比如,假如某块公地属于一个20至30户人家的村子,互相熟识,低头不见抬头见,这时候有人过度使用的话,道德制裁马上到——失去名誉,遭到村民排挤,整天有人在背后戳脊梁骨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公地悲剧也很难发生。所以公地不一定悲剧。 二、经济发展失衡、基础设施落后、外来人口增多等因素是两城环境与城市社区环境差异存在的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发展失衡和基础设施落后导致两城卫生环境糟糕,大家应该一看便知其中原因,在这里不赘述。 把外来人口看作两城卫生环境糟糕的原因,想必部分人无法接受。现在就对外来人口定义加以限制:外来人口,短期在某地居住的外来务工居民,无常住意愿。短期,根据不同行业,定义不同。 假设外来人口注意环境卫生,个人获得的净效益为20单位(其中10单位为实物或货币),给周围环境带来的收益为30单位;外来人口不注意环境卫生的净效益为10单位(其中15单位为实物或者货币,名誉损失为5单位),给周围环境带来的收益为15。结合外来人口的定义限制,它们的最优选择是不注意公共环境卫生或者打擦边球,因为此时他们的货币利益最大化。放松假设,这部分选择在总体选择中的比例也会占用很大的比重。
公地悲剧 一、公地悲剧定义 美国学者哈丁1968年在期刊《科学》上提出,公地悲剧是指当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资源,但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人使用,由此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即为“公地悲剧”。如草场过度放牧、海洋过度捕捞等。 二、案例导入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位于湖南省西北部,由张家界、天子山、索溪峪三大各具特色的风景区组成,是我国首批公布的国家级森林公园,被誉为“大自然迷宫”和“天下第一奇山。”武陵源1998年被国务院省定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年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地质公园。 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高,景区在发展和经营中采取了“强化旅游设施建设,弱化遗产资源的保护”方式导致了武陵源游客蜂拥而来,总收入呈阶梯状攀升,景区有限的旅游环境容量与过度增长的游客人数之间的矛盾也突显出来。由于武陵源景区的旅游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当地居民转变过来,整体素质低下,“经济导向”十分明确:在景区内修建索道和电梯,强行炸毁小山头;在天子山自然保护区强行乱占滥建,加修门面和修建猪舍;在天子山神堂湾砍伐林木10立方米。生态保护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相对薄弱。随着人们对资源的过度性开发和掠夺性索取,导致武陵源受到严重的破坏,形成典型的“公地悲剧”。 三、相应的对策建议 1、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层次多类别的治理模式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考虑到世界遗产资源的稀缺性、公共性和受保护性,应该强调的是把公地悲剧理论的三种主要的治理方式结合,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结合“政府强权治理”、“上市公司治理”和“多中心自主管理”这三种方式。对世界遗产不仅要实行两权分离,更重要的是在现阶段实行政府的强权管理。同时将世界遗产进行合理的功能区划,如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试验区。核心区是世界遗产的主要精华和意义所在,要严格禁止一切外界的干扰。缓冲区一部分可对游客开放。实验区是开展旅游活动最主要的区域。通过政府的强制管理,来约束景区的管理,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规范旅游秩序,进一步完善旅游市场。 2、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 为了更好的保护景区资源,有必要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同时严格执行相关的法律文件,依法保护遗产资源。对于景区而言,要划分好景区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关系,这既避免了独断专行,同时也明确了各自的职能分工,为景区的旅游监督和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通过各种形式来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推进遗产地景区旅游事业的发展。 3、提高公民的保护意识 在游览景区过程中,人们缺乏“公共意识”是导致“公地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人人都认为既然这块地是公共的或公家的,就不是自己的,用不着自己负责。通过宣传,提高公民的保护意识,能做到严于律己。对于景区而言,可以制定一些奖惩措施,用一些规范化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他们有意识去保护公地。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出面公布公地具体维护的成本,这是让每个公民成
掉在地上的钞票为什么没有人捡? 美国经济学界多年前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 有一天,一位学富五车的经济学者教授和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助理教授一起外出吃午饭。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眼尖的年轻教授发现地上有张100美元的大面额钞票,便弯下腰准备把它捡起来。不料,那位老教授立刻出手拦住他说:“别捡了,这钞票是假的。”年轻教授不服气、问道:“你如何断定这钞票是假的?”老教授随口回答:“如果这100元的钞票是真的,早该被人拾走了。” 老教授的答案虽然书呆得可笑,但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答案。市场的高效率保证它时时出清,谈判桌上没有剩下的钱,人行道上也不可能有还未被捡走的钞票。在老教授看来,年轻教授是经济学修养不够才会伸手去捡那掉在地上的钞票。 掉在地上的钞票之所以没人捡,当然还有捡不来、不让捡、捡了也白捡等其他原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种种浪费现象.其实就和钞票掉地上没人捡一样。我们的无奈等待,其实还是和“捡不来、不让捡、捡了也白捡”分不开。 奥尔森1996年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大面额钞票掉在人行道上没人捡: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的文章。他认为,能够在国家这一层次上解释贫富差别的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资源的禀赋不同。二是公共政策和体制不同。奥尔森的结论是、决定国家贫富的主要因素不是包括技术、知识、土地、资金和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票赋,而是一个国家的体制和公共政策以及影响体制与政策质量的公共物品型人力资源。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有亿万元钞票掉在地上没人捡!要捡起这巨额钞票,必须靠千万人的分工、合作,必须有对私人产权的绝对保护以及对合同的公正实施。好的体制和政策能够保证对产权长期有效的保护,杜绝任何形式的掠夺,激励人们从事分工、合作的创新生产活动,特别是“产权密集型”的生产活动。“掉地上的钞票”之所以“捡不来”、“不让捡”或者“捡了也白捡”,关键是体制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钞票掉在人行道上没人捡的事确实也不少见.莫斯科街道上前些年就出现过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沿街的店铺大量空置;另一方面,街道夯涌现出许多金属做成的箱形销售摊。在高峰期的1993年、莫斯科街道上有1.7万只这样的金属箱子,一眼望去就像是置身于金属森林之中。为什么在莫斯科寒冬里沿街叫卖的商贩不搬到温暖的店铺里去?为什么沿街店铺的拥有者要放弃可观的租金收入?为什么掉在街边的钞票多年没人捡?密执根大学一位叫黑勒的年轻教授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于1998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反公地悲剧”的概念。 大家也许对“公地悲剧”的概念较为熟悉。 “悲剧”的产生是由“公地”的产权特性所决定的。“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而且没有人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结果是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放牧的草原、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以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它们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黑勒的反公地有相反的产权特性。反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也有许多拥有者,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资源,而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反公地”的产权特性是给资源的使用设置障碍,导致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足,造成浪费。就像在一间房子的大门上安装需要十几把钥匙同时使用才能开启的锁,这十几把钥匙又分别归十几个不同的人保管,而这些人又往往无法在同一时间到齐。显而易见,打开房门的机会非常小,房子的使用
1968年英国加勒特·哈丁教授(Garrett Hardin)在《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中首先提出“公地悲剧”理论模型。 他说,作为理性人,每个牧羊者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在公共草地上,每增加一只羊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获得增加一只羊的收入;二是加重草地的负担,并有可能使草地过度放牧。经过思考,牧羊者决定不顾草地的承受能力而增加羊群数量。于是他便会因羊只的增加而收益增多。看到有利可图。许多牧羊者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由于羊群的进入不受限制,所以牧场被过度使用,草地状况迅速恶化,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界定产权的交易成本太高)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本质就是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悲剧”的产生是由“公地”的产权特性所决定的。“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而且没有人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结果是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放牧的草原、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以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它们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说到哈丁的“公地悲剧”或日“公有资源的灾难”,那是对个人在利用公共资源时存有私心的确证。哈丁将这一状态模型化:一个向众人开放的牧场,在其中每个牧羊人的直接利益取决于他所放牧的牲畜数量的多少。由于在缺乏约束的条件,当存在过度放牧问题时,每个牧羊人虽然明知公地会退化,但个人博弈的最优策略仍然只能是增加牲畜数量,久而久之,牧场可能彻底退化或废弃。这就是“公地悲剧”。“公地悲剧”的发生,人性的自私或不足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而公产缺乏严格而有效的监管是另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公地悲剧”并非绝对地不可避免。 “公地悲剧”展现的是一幅私人利用免费午餐时的狼狈景象——无休止地掠夺。“悲剧”的意义就在于此。根据哈丁的讨论,结合我们对挣扎在生活磨难中的人们的理解,“公地悲剧”的发生机理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勤劳的人为个人的生机而算计,在一番忽视远期利益的计算后,开始为眼前利益而“杀鸡取卵”,没有规则,没有产权制度,没有强制,最后,导致公共财产——那个人们赖依生存的摇篮的崩溃,所以,美国学者认为,公地悲剧发生的根源在于:“当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处置公共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发生。“公地悲剧”的更准确的提法是:无节制的、开放式的、资源利用的灾难。就拿环境污染来说,由于治污需要成本,私人必定千方百计企图把企业成本外部化。这就是赫尔曼·E.戴利所称的“看不见的脚”。“看不见的脚”导致私人的自利不自觉地把公共利益踢成碎片。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公地悲
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 当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资源,但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人使用,由此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即为“公地悲剧”。如草场过度放牧、海洋过度捕捞等。 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反公地悲剧【Tragedy of Anti-Commous】 1998年,美国黑勒教授(Michael·A·Heller)在《The Tragedy of Anti-Commous》一文中提出“反公地悲剧”理论模型。他说,尽管哈丁教授的“公地悲剧”说明了人们过度利用(overuse)公共资源的恶果,但他却忽视了资源未被充分利用(underuse)的可能性。在公地内,存在着很多权利所有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每个当事人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该资源或相互设置使用障碍,而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导致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足,造成浪费,于是就发生了“反公地悲剧”。 二者的区别概述 公地与反公地“悲剧”的本质在于产权问题。产权一般具有两种形态:公共产权和私人产权。当某种资源为某个人单独所有时,该资源为私人财产,其产权为私人产权。它具有产权制度边界清晰、产权归属明确,所有权效率高的特点。当某种资源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所有时,称为公共财产,其产权为公共产权。它具有以下特点:在消费规模上没有限制,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这项资源的权益,所以存在收费困难;每个当事人天然享有资源权益,无需采取交费申请加入的方式;每一当事人在使用该资源时,会影响和损害其他成员的利益,即存在外部性。由于该资源向每个社会成员开放,允许他们自由进入,平等分享,并获取平均利益,因此,搭便车和产权拥挤现象就难以避免。鉴于权利是相互排斥的,对于稀缺资源来说,公共产权要么造成资源的过度利用(“公地悲剧”),要么造成资源利用不足(“反公地悲剧”)。 产生原因不同。“公地悲剧”的产生是由于公地上任何人都没有排斥其他人同时使用的权力,而“反公地悲剧”产生则是由于公地上任何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不让别人正常使用的权力。结果有所差别。“公地悲剧”导致的是资源过度利用,而“反公地悲剧”导致的则是资源的无效、低效,甚至根本不能利用。或者换句话说,“公地悲剧”导致的是大量的“搭便车”,而“反公地悲剧”导致的是车上的座位部分的甚至是完全的空置,没有被充分利用。第三,解决办法不同。“公地悲剧”因为产权虚置、不明晰,所以需要明晰产权。“反公地悲剧”因为产权支离破碎,故需要整合产权。 两种“悲剧”在农村旅游中的现状分析 公地的本质特征在于决定使用方式的产权结构,也就是说,并非只有自然资源才能成为“公地”。如果某种资源的产权安排决定了很多人都能不同程度地使用这种资源,那么这种资源就具有公地的特性。据此理解,公地的范围就可以从自然资源扩展到企业界等。我国现
公地悲剧案例分析 Document number:PBGCG-0857-BTDO-0089-PTT1998
“特产”的公地悲剧案例分析 一、什么是公地悲剧 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而每一个人都倾向于过度使用,从而造成资源的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这一个概念经常运用在区域经济学,跨边界资源管理等学术领域。 二、地方特产的危机 地方特产作为一种典型产品,既发挥着标志作用,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支撑力量。但在对待特产这件事上,一些知名地方特产正在遭受价值掠夺,有陷入“公地悲剧”的危险。 由于特产的地域特点很强,北京的烤鸭、西藏的冬虫夏草、宁夏的枸杞、山东的大花生、新疆的葡萄……许多土特产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起到显着的影响,而这些为土特产提供市场价值的地域属性极易成为一块“公地”。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金华火腿、龙口粉丝、太仓肉松等不少知名地方特产因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接连被媒体曝光,便是典型的“公地悲剧”。不管跟这些土特产的产地沾不沾边,人人都想沾“公地”的光,都抱着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的态度,搭车寄生,鱼目混珠。结果是有人上树摘果,却无人浇水施肥。 三、如何防止公地悲剧 这些“公地悲剧”的发生,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目前全国各地都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加大对地方特产的管理保护力度。对土特产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无疑是一项极其有力的措施,这就像为土特产撑起了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地理标志既是产地标志,也是质量标志,更是一种知识产权。对地方特产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不仅有利于保证土特产的质量和特色,保护土特产品声誉,而且有利于促进其产业化、标准化生产发展,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 在我看来,面对公地悲剧的问题,政府要通过管制或税收减少公有资源的使用来解决这个问题。自己的好东西如果自己不懂珍惜,即使别人抢不走,它们也会贬值乃至损毁。因此,各地一定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地方特产的地理标志保护工作,让它们在养好一方人,发展一方经济的同时,吸引更多人来分享。
共有地的悲剧 我们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国家的居民在为环保而游行示威。其中参与者最为投入的是一些社区的居民为反对某个有污染的或令人厌恶的设施而进行的抗议。在一些生活富裕的地区,人们开始更多地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一些公共设施如加油站、变电所、垃圾处理场,以及污染性火电厂、核电厂的建设,都难免要与当地居民发生剧烈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虽然抗议的形式和对象各不相同,但所发出的呼声是一致的:“不要在我家后院……” 这就是真实的人性反应,抗议者不仅是在呼吁环保,而且是在维护自己的环境权不受侵犯。换言之,所谓环境问题绝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还必然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自然已经被资源化,由不同的人使用,使用者的价值取向、利益抉择不同,决定了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的不同,因此,具体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是不同利益群体以自然和技术为中介的社会关系。 最能够体现人的自私的本性是人们对待公共资源的态度。每个人家里的水池都是非常干净的,至少畅通吧,可公共食堂的水池却几乎永远都是堵塞的。人类生物学家盖瑞?哈定(G arret Hardin)将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共有地的悲剧”。 图7.1 哈定 1968年,美国加州大学的哈定教授就人口资源等问题撰写了一篇题为“共有地的悲剧”的论文,深刻地说明了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和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导致共有资源枯竭的问题。“共有地悲剧是一个具有一般性结论的故事:当一个人使用共有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使用。由于存在这种负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当今社会,
资源的枯竭,环境质量的退化,与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和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共有地的悲剧”这个典故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英国。那时,大多数村庄的边缘都有一片“共有地”。附近的村民都可以在上面放牧。如果他们能够明智地使用这些共有地,就可以逐渐增加自己的财富。但是,人口增加以后,出现了过度放牧的现象,许多共有地终遭毁坏。 假想在一块共有地上,最高的牧养能力为100头牛,有10名村民在放牧,每人有8头牛。这时,每在共有地上多放牧一头牛,就可以增加村民的个人财富,而不会伤害到他人。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可以假定,每个人都有10头牛,大家从共有地上获得了最大的实利——假定为100个单位的财富。如果再增加牛的数量就会使影响草的生长,对大家不利。但是,因为共有地没有人进行管理,人们仅从自己的立场进行盘算,他们只知道谁增加牛的数量,谁就多得一份利益,而只分担公共利益中的一部分损害。哈定在《共有地的悲剧》中写到: 农夫们的结论是,他们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再加进一头牛。再加一头:再加一头……但这是每一个农夫所个别做出的结论。每个人都被锁入一个体系而被迫使他必须无限制地扩增自己放牧的牛的数量……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急急忙忙地自取灭亡,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高利益,且相信这是共有地的自由。共有地上的自由会导致群体的败亡。 图7.2 共有地图片一
一,公地悲剧概述 哈丁在《公地的悲剧》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牧民将如何取舍?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 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 --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公地悲剧在英国是和“圈地运动”联系在一起的。15,16世纪的英国,草地、森林、沼泽等 都属于公共用地,耕地虽然有主人,但是庄稼收割完以后,也要把栅栏拆除,敞开作为公共牧场。由于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养羊业飞速发展,于是大量羊群进入公共草场。不久,土 地开始退化,“公地悲剧”出现了。于是一些贵族通过暴力手段非法获得土地,开始用围栏将公共用地圈起来,据为己有,这就是我们历史书中学到的臭名卓著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使大批的农民和牧民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土地,历史书中称之为血淋淋的“羊吃人”事件。但是书中没有提到:“圈地运动”的阵痛过后,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草场变好了,英国人作为整体 的收益提高了。由于土地产权的确立,土地由公地变为私人领地的同时,拥有者对土地的管理更高效了,为了长远利益,土地所有者会尽力保持草场的质量。同时,土地兼并后以户为 单位的生产单元演化为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劳动效率大为提高。英国正是从“圈地运动”开始, 逐渐发展为日不落帝国。 综上所述,工地悲剧的概念应当解释为:当一个人使用公有资源时,他就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公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政府可以通过管制或税收减少公有资源的使用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政府有时也可以把公有资源变为私人物品. 二,工地悲剧的成因 以模型化来解释,哈丁对于公地悲剧的成因研究巧妙的回答了如下:一个向众人开放的牧场,在其中每个牧羊人的直接利益取决于他所放牧的牲畜数量的多少。由于在缺乏约束的条件,当存在过度放牧问题时,每个牧羊人虽然明知公地会退化,但个人博弈的最优策略仍然 只能是增加牲畜数量,久而久之,牧场可能彻底退化或废弃。这就是“公地悲剧”。“公地悲剧” 的发生,人性的自私或不足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而公产缺乏严格而有效的监管是另一个必 要条件。所以,“公地悲剧”并非绝对地不可避免。 “公地悲剧”展现的是一幅私人利用免费午餐时的狼狈景象——无休止地掠夺。“悲剧”的意义就在于此。根据哈丁的讨论,结合我们对挣扎在生活磨难中的人们的理解,“公地悲剧”的
公共管理案例分析 王周 事件始末:2018年3月18日,江西省鹰潭市民夏女士通过问政鹰潭平台投诉,白露桥洞附近的荒地上垃圾成堆。对此,网友戏称“这是要建垃圾场的节奏啊”。随即,问政鹰潭平台以《鹰潭城区臭烘烘的“垃圾山”无人管》为题,予以曝光。对此,市城管局称该区域属月湖区管辖范围。而月 湖区城管局负责人 却表示,这片区域 属于市城管局管辖 范围,或者应该由 街道安排人员自行 清理,街道则表示 居民没有按时缴纳卫生管理费用。2018年4月4日,记者再次追踪调查,发现相关部门已着手整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垃圾常年堆积、清理难度大,预计清理工作将需一段时间来完成。 问题:思考如何解决城市公共管理中的“卫生死角”问题? 分析: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曾经断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本来干净的街道,直到堆积成为臭气扑天的垃圾山,直至影响周边居民日常生活与身体健康。案例中涉及到几个相关主体,包括市城管局、区城管局、街道和居民个人,相关管理部门推诿扯皮的“责任死角”在政府与市民心理之间活生生开辟出一道鸿沟。 英国科学家哈丁用“公地悲剧”描述了理性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体行为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恶果。在鹰潭市这块产权不明的公共用地上,社区居民乱倒垃圾,不缴费用的“搭便车”行为,街道办事处、城管部门、居民责任划分不清相互推诿的行为,使诸如垃圾清运之类简单的公共管理工作陷入了“集体行动的困境”之中。“我不做总有人去做”,社区居民将垃圾随手一扔,方便省事还不失动作潇洒;“别人出钱我不出,照样能办好”,拖欠乃至不缴卫生费用或期冀政府买单,每个理性居民的最优选择均是“不缴费”;“我不管总有人去管”,居民盼着社区管,社区盼着城管部门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是费力又费钱的公共事务。每个人都被困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追求自己 利益最大化的“纳什均衡”中,“尽管各方都有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但却始终没能明确各方的责任,无法形成解决问
公共地悲剧 “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是一种涉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Common good)对资源分配有所冲突的社会陷阱(Social trap)。这个字起源于威廉·佛司特·洛伊(William Forster Lloyd)在1833年讨论人口的著作中所使用的比喻。1968年时,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在期刊《科学》将这个概念加以发表、延伸,称为〈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而这个理论本身就如亚里斯多德所言:“那由最大人数所共享的事物,却只得到最少的照顾”。 牧民与草地的故事 有一个关于牧民与草地的故事,说的是当草地向牧民完全开放时,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有利润的。尽管因为平均草量下降,增加一头牛可能使整个草地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但对于单个牧民来说,他增加一头牛是有利的。可是如果所有的牧民都看到这一点,都增加一头牛,那么草地将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需要,导致所有牧民的牛都饿死。这个故事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哈定说:“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公有物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 公共地悲剧非正常的管理方法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哈丁转向寻求非科技或非资源管理的方法。 正面:牧羊人可以从增加的羊只上获得所有的利益负面:牧场的承载力因为额外增加的羊只有所耗损然而,牧场理论的关键性在于这两者的代价并非平等:牧羊人获得所有的利益,但是资源的亏损却是转嫁到所有牧羊人的身上。因此,就理性观点考量,每一位牧羊人势必会衡量如此的效用,进而增加一头头的羊只。但是当所有的牧羊人皆做出如此的结论,并且无限制的放牧时,牧场负载力的耗损将是必然的后果。于是每一个个体依照理性反应所做出的决定将会相同,毕竟获得的利益将永远大于利益的耗损。而无限制的放牧所导致的损失便是外部性的一个例子。 公共地悲剧永无休止的悲剧
公地悲剧 一、科学涵义: 公地悲剧是一种现象的简称。它是由美国学者哈丁于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的文章中提出来的。 公地悲剧将注意力集中于人口的增长和地球资源的合理使用,即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有限资源为生活质量所带来的影响。如人口成长最大化,那么每一个个体必须将维持基本生存之外的资源耗费最小化。 二、哈丁在《公地的悲剧》中设置的场景: 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上放牧。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 如果每个牧民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每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三、公地悲剧与“圈地运动” 公地悲剧在英国是和“圈地运动”联系在一起的。15-16世纪的英国,草地、森林、沼泽等都属于公共
用地,耕地虽然有主人,但是庄稼收割完以后,都要把栅栏拆除,敞开作为公共牧场。 由于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养羊业飞速发展,于是,大量羊群进入公共草场。不久,土地开始退化,“公地悲剧”出现了。于是,一些贵族通过暴力手段获得土地,开始用围栏将公共用地圈起来,据为己有,这就是我们历史书中学到的臭名卓著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使大批的农民和牧民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土地,历史书中称之为血淋淋的“羊吃人”事件。 但是,书中没有提到:“圈地运动”的阵痛过后,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草场变好了,英国人作为整体的收益提高了。 由于土地产权的确立,土地由公地变为私人领地的同时,拥有者对土地的管理更高效了,为了长远利益,土地所有者会尽力保持草场的质量。同时,土地兼并后,以户为单位的生产单元演化为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劳动效率大为提高。英国正是从“圈地运动”开始,逐渐发展为日不落帝国。 这不是想为“圈地运动”平反,因为从道德伦理上讲这是一段血腥的历史。但是,如果没有“羊吃人”事件,最终的结局将是整体毁灭。现在世界上土地保护好的地方,往往都建立了土地产权,而那些土地破
4.结论是,最佳人口数量应该是小于最大量的。但是怎么定义这个最佳量目前还是未能解决的问题。 作者说,希望每个人得到最大的利益,但是利益是什么呢?理论上利益也许无法衡量,但是现实中却可以,只需要一套评价准则和一个衡量系统。 5、公地的悲剧 用牧民放羊来论证公地的悲剧,(可以做折线图)让我们想象一块对所有人都开放的草地。在这块公共地上每一个牧人都会尽可能多地放牧他的牲畜。作为理性人,每一个牧人都期望他的收益最大化。不管直白还是隐晦,或多或少地他都会问,“给我的兽群多增加一头牲畜,对我来说有什么效用?”这个效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影响。 (1)正面的影响是使牧群总量增加了。因为这个牧人能通过变卖这头额外的羊得到全部的收益,所以效用几乎能达到+1。 (2)负面的影响是由这额外的一头羊所引起的过度放牧。因为不管怎样,过度放牧是由所有的牧人承担的,负面效用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小部分-1。 将所有的影响加总,理性的牧人会得出结论:对于他来说,使他的牧群多增加一头牲畜是个明智的选择。但是其他每一个共用这块草地的理性的牧人也会得出如此结论。所以悲剧就发生了。每一个人都陷入到一个促使他无限制地增加牲畜数量的机制当中,而他们所处的世界是有限的。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的社会里,每一个追逐个人利益的人的行为最终会使全体走向毁灭。公地自由会毁掉一切。 列举了马萨诸塞州的圣诞节塑料袋案例和国家公园的案例。又提出最近西部山区的牧羊人乡政府施压要求增加放牧数量、公共海洋的案例。以国家公园来说,公园本身是有限的,但是人数似乎是无限制地增加,公园的价值对游客来说就是逐渐减少的。坦白说,我们必须立即停止将公园当作公地对待,否则它们对于任何人将毫无价值可言。 作者发问,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有几个选择。我们可以把公园变卖使之成为私人财产,我们也可以继续把它们当作公有财产但分配进入公园的权力。否则,我们只能放任作为公地的国家公园不断遭受破坏。 6.污染 从反向的方法来看,公共地悲剧在污染问题中是重新出现的。其效用的计算还是和之前一样,理性的人会发现他向公共地排放垃圾后,自己所承担的成本要小于排放垃圾前为它们作净化处理所承担的成本。因为这在每一个人看来都是正确的,所以只要我们像独立、理性而自由的企业家那样行事,我们就会陷入到一个“污染自家”的怪圈。 提出解决方法---通过私人产权,或者类似的形式可以避免像食品篮子似的公共地悲剧。但我们周围的空气和水源却无法通过这种形式得到保护,所以必须靠另外的方法避免另一种如同污水池的公地悲剧,比如可以通过强制的法律手段或税收机制使排污者自己处理垃圾的成本小于不作任何处理就丢弃垃圾的成本。(当时)对于这两种悲剧我们都还未取得任何进展 又提出,污染问题是由人口问题引起的,所以,人多资源少,就需要对产权重新界定。 7、怎样制定自律法律?如何通过立法来节制?
公共草地的悲剧 禾木 在我学习过的美国马萨诸塞州阿美土德小镇的中心,有块挺大的草坪,镇上所有的大型户外活动像庙会、图书节、周末免费的流行音乐会等都在这里举行。人们在草地上散步、玩飞盘、打排球,孩子们在草地上追逐打闹游戏,格外开心。 我纳闷为什么这块草地竟然能保存到现在,因为草地附近全是停车场、商店、餐厅和住宅c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得知这块普普通通的草地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公共绿地",几乎家喻户晓的典故"公共草地的悲剧"就起源于它。 在过去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几乎所有的城镇中心都有这么一块公共草地,城镇里的室外集体活动都在草地上举行。那时的美国,家家户户都很注重实惠,自己种菜,养鸡鸭牛羊什么的。草地空着时,就有人在那儿放羊。没有人在意草地上的草为什么总长不好。 到了1968年,有个叫哈丁的人抽时间琢磨了一下公共草地的问题,不琢磨不知道,他居然从平常的草地里发现了大问题,经过归纳总结,写了篇《公共草地的悲剧》的文章,发表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 哈丁认为公共草地永远长不好,最终只能是一场悲剧。因为公共草地归集体所有,但人们在草地上放的是私人的羊,卖羊的收入归个人所得。毫无限制地在草地上放羊,必然造成草地退化,但草地退化带来的损失却是由全镇(纳税)人平均负担。如果镇上的人口很多,平均下来每个人摊到的草地损失虽说没有多少,但养羊大把大把的收入却揣进了个人腰包,放羊越多,得的便宜就越大。有些人没住在草地边上,无法放羊,却同样承担这种损失。 哈丁认为,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人的想法是拼命地利用草地,放的羊越多越好,争取在草地彻底完蛋之前多捞一点。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公共草地怎能长好?因此他最后的结论是:如果使用公共资源来为个人谋私利,"公共草地的悲剧"是无法避免的。 当时哈丁借用这个例子去分析人口增长和环境污染问题。
公地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公地的悲剧 by Garrett Hardin, 1968 Published in Science, December 13, 1968 At the end of a thoughtful article on the future of nuclear war, Wiesner and York (1) concluded that: "Both sides in the arms race are ... confronted by the dilemma of steadily increasing military power and steadily decreasing national security. It is our considered professional judgment that this dilemma has no technical solution. If the great powers continue to look for solutions in the are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ly, the result will be to worsen the situation." J.B. Wiesner和H.F. York在一篇关于核子战争前景的发人深省文章结尾时说:「武器竞赛的双方都是…面对持续增强的军事力量和持续减弱的国家安全。深思之下,我们的专业意见认为这困局没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如果大国只是在科学和科技这方面找寻解决办法,结果只会令情况恶化。」 I would like to focus your attention not on the subject of the article (national security in a nuclear world) but on the kind of conclusion they reached, namely that there is no technic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An implicit and almost universal assumption of discussions published in professional and semipopular scientific journals is that the problem under discussion has a technical solution. A technical solution may be defined as one that requires a change only in the techniques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demanding little or nothing in the way of change in human values or ideas of morality. 希望各位不要集中注意文章的主题(核武世界的国家安全),而是要留意作者的结论,即是问题没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专业和半通俗科学期刊的评论,差不多都隐喻评论的问题是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技术性解决办法可以定义为只要改变自然科学的技术,无需或只是稍为改变人的道德价值或概念。 In our day (though not in earlier times) technical solutions are always welcome. Because of previous failures in prophecy, it takes courage to assert that a desired technical solution is not possible. Wiesner and York exhibited this courage; publishing in a science journal, they insisted that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was not to be found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They cautiously qualified their statement with the phrase, "It is our considered professional judgment. . . ." Whether they were right or not is not the concern of the present article. Rather, the concern here is with the important concept of a class of human problems which can be called "no technical solution problems," and, more specifically,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and discussion of one of these. It is easy to show that the class is not a null class. 我们现在一般都欢迎有技术性解决办法(以前并非如此)。因为以前的预言往往失准,要有莫大勇气才会断言没有预期的技术性解决办法。Wiesner和York表现出勇气,在科学期刊发表文章,坚持问题不能在自然科学找到解决办法。他们小心翼翼为声明加上以下的批注:「深思之下,我们的专业意见…。」本文所关注的。不是他们是否正确,而是一个重要的观点:有一组关乎人的问题可以称为「没有技术性解决办法的问题」,或是更明确地说:认定和讨论这些
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Garrett Hardin (1968) 英语原文https://www.doczj.com/doc/d42572461.html,/cmt/tragcomm.htm Garrett Hardin,〈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科学Science》162(1968):1243-1248页(CC)(BY)翻译:马景文(自学书院,2006年) 译注:这是一篇公开取阅的翻译论文,根据「创作共享理念授权同意书」 (https://www.doczj.com/doc/d42572461.html,/licenses/by/2.0) 的条款发表,并准许无限制使用,分发和以任何形式复制作非商业用途,但必须注明原译文出处和译者。 作者在1993年发表同名文章,提出更多例证。译文参见 https://www.doczj.com/doc/d42572461.html,/depository/env_tragedy_commons_hardin_1993_tc.doc J.B. Wiesner和H.F. York在一篇关于核子战争前景的发人深省文章结尾时说:「武器竞赛的双方都是…面对持续增强的军事力量和持续减弱的国家安全。深思之下,我们的专业意见认为这困局没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如果大国只是在科学和科技这方面找寻解决办法,结果只会令情况恶化。」1 希望各位不要集中注意文章的主题(核武世界的国家安全),而是要留意作者的结论,即是问题没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专业和半通俗科学期刊的评论,差不多都隐喻评论的问题是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技术性解决办法可以定义为只要改变自然科学的技术,无需或只是稍为改变人的道德价值或概念。 我们现在一般都欢迎有技术性解决办法(以前并非如此)。因为以前的预言往往失准,要有莫大勇气才会断言没有预期的技术性解决办法。Wiesner和York表现出勇气,在科学期刊发表文章,坚持问题不能在自然科学找到解决办法。他们小心翼翼为声明加上以下的批注:「深思之下,我们的专业意见…。」本文所关注的。不是他们是否正确,而是一个重要的观点:有一组关乎人的问题可以称为「没有技术性解决办法的问题」,或是更明确地说:认定和讨论这些问题是其中之一。 要表明这类问题不是空号很容易。还记得划井游戏。想一想:「我如何赢划井游戏?」假设(依照赛局理论的惯例)我的对手是个中能手,大家都知道我不可能赢。换句话说,问题没有「技术性解决办法」。要赢,我只能把「赢」的意义根本改掉。我可以打对方的头,可以弄虚作假。每一种我要「赢」的方法,都是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我们认知了解的游戏。(我当然可以公开放弃—不玩。大多数成年人都这样。) 「没有技术性解决办法的问题」有其它的命题。我的论题:大家惯常认知的「人口问题」是这样的命题。要说明一下大家是怎样惯常认知的。持平的说,大多数人为人口问题苦恼,要找出方法避免人口过多的邪 1J. B. Wiesner 与H. F. York, 《科学美国Scientific American》211 (第4号), 27 (1964).